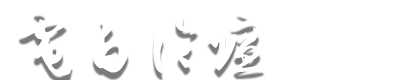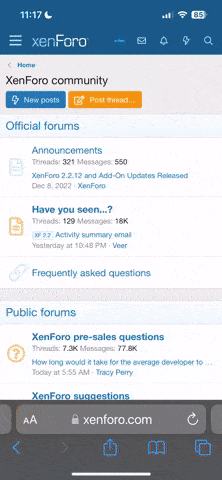-
论坛网址:https://db2.mom(可微信分享)、https://0668.es、https://0668.cc(全加密访问)
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交流 绮梦阁,技师,星空,小行,诗人,小石教师 (42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夏哥兄弟
- 开始时间
夏哥兄弟
荣誉主席
- 注册
- 2008-10-30
- 帖子
- 4,725
- 反馈评分
- 541
- 点数
- 191
-
Windows 10 Chrome 133.0.0.0
- #2,190
《风纪扣》
小石龟在单位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衣冠者,他穿白衬衣从不打领带,但一丝不苟的会把纽扣全扣上包括风纪扣,就像一只装在闺房里照顾得一丝不苟的宠物狗。
小龟的白衬衫总像浸过明矾水似的,领口直挺挺戳着喉结,仿佛要替他发出些声响来。教学楼一楼楼道的穿堂风路过他时总打个趔趄——那排扣得严丝合缝的纽扣,原是铁打的栅栏,连教师饭堂的不锈钢门都要给小龟点面子。
同事小月偷偷数过小龟的纽扣,七粒,不多不少,说,龟哥,你的纽扣七粒,像七枚铜钱串成的符咒,是否镇着200小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魂灵。阿龟不可置否,同事间里飘着的闲话,说小石龟15年前在读书期间在大学旁边的道观里跟一个叫做鬼米子的道士学过易经学过风水学过奇门遁甲学过玄学,毕业后又去北方当过一年仪仗兵,连呼吸都卡着秒表;也有人说他母亲的亲戚的亲戚或是他母亲表哥的三表妹的二女儿是裁缝,在给小龟量身定做的白衬衣上用顶针钉死了他最后一粒纽扣。真真假假的流言撞在原教务部101室的铁皮柜上,叮叮当当落了一地像是龟甲,但不是鸡毛。
200小单位大院里开表彰会或教学会或创文巩卫会或座谈会那天,4哥4少的领带被西风和风扇风和空调风等混合风撩得翻飞。小龟端坐在前排,脖颈处那道月牙形的勒痕在阳光下泛着青白。同事的领带都在风里跳弗朗明戈,唯有他的衣领如刑枷般焊在皮肉上。春蝉在学校2002年栽种的香樟树上笑得发抖,汗珠顺着小龟的鬓角往下淌一直到颈该,竟也规规矩矩排成纵列,每个与会者面前就有一包抽了一半左右的维达面巾纸,但小龟懒得用左去抽来抹汗。
有人(据说是小行)见过小石龟午休时在绮梦阁对着一楼楼梯上半部的镜子调整领口,或借玻丽的手机用镜子模式咧咧嘴,枯枝般的手指在喉结处反复摩挲,仿佛要拧紧某个看不见的发条。绮梦阁另一端洗脚房玻璃窗外的木棉花扑簌簌地落,在他的白衬衫上洇出点点锈迹——原是扣得太紧,血沫子从牙龈渗出来了。
暮色漫进办公室时,小龟立在阳台上解风纪扣。铜纽扣咬住最后一缕天光,发出咯吱咯吱的钝响,像生锈的怀表链条突然开始倒转。太阳能路灯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他脖颈上有道淡青的痕,蜿蜒如未拆线的伤口。
广州红双喜香烟的火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小龟在风中又点了一支烟,他抽一口,让风吹一口,就这样,风抽着小龟的烟,小龟抽着风。烟灰簌簌落在他白衬衫第三粒纽扣的位置,那粒扣子不知何时竟松开了,露出截苍白的皮肉,像铁笼里突然漏了道缝。
小石龟在单位是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衣冠者,他穿白衬衣从不打领带,但一丝不苟的会把纽扣全扣上包括风纪扣,就像一只装在闺房里照顾得一丝不苟的宠物狗。
小龟的白衬衫总像浸过明矾水似的,领口直挺挺戳着喉结,仿佛要替他发出些声响来。教学楼一楼楼道的穿堂风路过他时总打个趔趄——那排扣得严丝合缝的纽扣,原是铁打的栅栏,连教师饭堂的不锈钢门都要给小龟点面子。
同事小月偷偷数过小龟的纽扣,七粒,不多不少,说,龟哥,你的纽扣七粒,像七枚铜钱串成的符咒,是否镇着200小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魂灵。阿龟不可置否,同事间里飘着的闲话,说小石龟15年前在读书期间在大学旁边的道观里跟一个叫做鬼米子的道士学过易经学过风水学过奇门遁甲学过玄学,毕业后又去北方当过一年仪仗兵,连呼吸都卡着秒表;也有人说他母亲的亲戚的亲戚或是他母亲表哥的三表妹的二女儿是裁缝,在给小龟量身定做的白衬衣上用顶针钉死了他最后一粒纽扣。真真假假的流言撞在原教务部101室的铁皮柜上,叮叮当当落了一地像是龟甲,但不是鸡毛。
200小单位大院里开表彰会或教学会或创文巩卫会或座谈会那天,4哥4少的领带被西风和风扇风和空调风等混合风撩得翻飞。小龟端坐在前排,脖颈处那道月牙形的勒痕在阳光下泛着青白。同事的领带都在风里跳弗朗明戈,唯有他的衣领如刑枷般焊在皮肉上。春蝉在学校2002年栽种的香樟树上笑得发抖,汗珠顺着小龟的鬓角往下淌一直到颈该,竟也规规矩矩排成纵列,每个与会者面前就有一包抽了一半左右的维达面巾纸,但小龟懒得用左去抽来抹汗。
有人(据说是小行)见过小石龟午休时在绮梦阁对着一楼楼梯上半部的镜子调整领口,或借玻丽的手机用镜子模式咧咧嘴,枯枝般的手指在喉结处反复摩挲,仿佛要拧紧某个看不见的发条。绮梦阁另一端洗脚房玻璃窗外的木棉花扑簌簌地落,在他的白衬衫上洇出点点锈迹——原是扣得太紧,血沫子从牙龈渗出来了。
暮色漫进办公室时,小龟立在阳台上解风纪扣。铜纽扣咬住最后一缕天光,发出咯吱咯吱的钝响,像生锈的怀表链条突然开始倒转。太阳能路灯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他脖颈上有道淡青的痕,蜿蜒如未拆线的伤口。
广州红双喜香烟的火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小龟在风中又点了一支烟,他抽一口,让风吹一口,就这样,风抽着小龟的烟,小龟抽着风。烟灰簌簌落在他白衬衫第三粒纽扣的位置,那粒扣子不知何时竟松开了,露出截苍白的皮肉,像铁笼里突然漏了道缝。
正在浏览此帖子的用户
当前在线: 43 (会员: 0, 游客: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