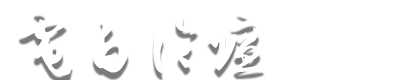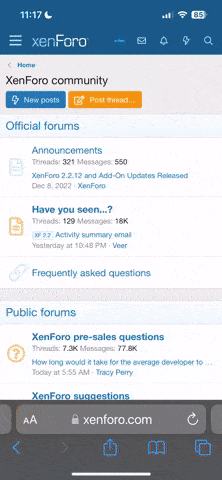文革中的电白二中
十年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电白县第二中学风雨飘摇,伤痕累累。笔者记下它的遭遇,意在让昔日同窗、日后的学棣,牢记住这历史的创伤。
那时的二中,从规模、师资、设备皆与电白一中相等,是电白仅有的两所完中之一,生源主要源于麻岗、大衙、林头、羊角、下垌、黄岭、观珠、沙琅、罗坑、那霍、望夫一带。六一年前为九个班(即初中每级二班、高中每级一班)、六二年后高中不变,初中增收两个班。到六四年,二中便成为初中十二个班。共高中十五个班,约七百多人的学校。这段时间,学校的教师约四十人多人,职员六人,校长谢克明、教导主任冯宗钦、工会主席李德发。
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二中便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文革浪潮之中。先是成立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文革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开展运动。如发展红卫兵、破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大字报上街。此外,文革的任务还要在教师中定下黑帮分子、选送六次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名单。文革的成员是由县委工作组指定的部分出身好的学生。他们代表了当时学校的最高权力。七月,暑假将至时,全校学生卷入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热流。他们一般是以班为单位。多则七八十人,少则十多人,步行全国各地,大部分到广州,个别人到北京。约近百人到了毛主席的故乡湖南韶山。九月,大串连结束。全校同学返校闹革命。学生们把各地的经验带回学校。于是,学生们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一般称为战斗兵团或造反大队。如高四(当时高考停止招生,他们毕业后返校闹革命)为“烈火“战斗兵团、高三为”延安“战斗兵团、高二为”红闯“战斗兵团。高一为”一二•九“造反队、初三、初一为”红旗“战斗兵团、初二则有”东风“、”文锋“、”星火“等战斗兵团。此外,还有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如”燎原“、”井冈山“、”独立“、”鲁迅“、“五四”、“红卫”、“欧阳海”、“三二一一”等。当时众多的红卫兵组织中,队伍最庞大、战斗力最强的是“红旗”兵团,“延安”、“烈火”则次之。“东风”、“文锋”联合为“东文总部”,亦是较活跃的组织之一。
当时的教师划分为三个等级,部分出身好的,如陈作达、林文锐、何佛根,刘经超、张其亦、关中元、程为东等老师,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较为自在;部分出身不够好的,不受太大的冲击。红卫兵们组织他们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如崔民佣、温和、温文让、唐济林、庞桂秋、冯宗钦、林中亚、谢盘铭、王莲秀等老师。部分出身差的却受批斗,带高帽挂牌游街,列入黑帮行列,完全失去自由,如崔南屏、李德发、高川若、刘东勃等老师。其中最惨为李德发和高川若。一段时期的批斗后,由文革开除出教师队伍,送返家乡参加生产劳动。校长谢克明也受到批斗,但冲击不大。李德发回乡后,没有旧屋居住,只好搭起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的茅屋,与其子李柯居住,后遭火灾,茅屋与简单的家具焚之一炉。好长一段时间,父子二人借居生产队的队屋里,生活过得异常艰苦。高川若厄运临头,这位大学时候参加革命,后留学德国、日本的学者,元帅聂荣臻、日本首相田中的同窗挚友,回乡后不到两个月,便被贫下中农“专政”,用锄头活活砸死,其惨不可言。这事惊震甚大,后来,周恩来、聂荣臻闻此事都十分气愤和惋惜。七一年田中访华,在北京知道消息后,即时为他默哀了三分钟。高川若的平生,后来已载入电白县县志。
红卫兵组织均受文革的领导。各自司令部(办公室)设在相应教室里,任务是组织和参加一些批斗会,写大字报,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调查搜集和揭露黑帮“罪状“等。另一个热潮是:部分学生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演出,其机构均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排练文娱节目,到各地演出。这样的组织有竟达四个之多,其中是《欧阳海》宣传队、《红卫》宣传队、《长征》宣传队、《三二一一一》宣传队。每个宣传队的节目都达三四十个,足足可演三个小时。演员、乐器水平几乎都达专业水准。他们穿州过县,频频演出。比如《欧阳海》宣传队,一个月曾巡走四个县,上演二十二晚,比当时的专业剧团演出还多。此外,还有些组织也积极参与,排练大量节目,但不外出演出,只参加当地的一些演出,如《红旗》兵团、《一二九》造反队等。这段时间,二中造就了大量文娱人才。
一段时间后,文革因执行所谓错误路线(当时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工作组长赖良到二中作检讨。学校掀起了批判文革的高潮,主要以《烈火》、《红旗》为主力。从此,文革解散,各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不受束缚。但因文革的主要成员都在《延安》,而导致《延安》与《烈火》、《红旗》不和。
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红卫兵组织,即电白县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五司令部(简称红五司,当时一中成立一司,电白供销系统成立二司,邮电、水电等系统成立三司,四司则为水东地区的工人组织)。红五司以《红旗》、《烈火》、《东文》、《星火》为核心,组织六区各镇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约两千多人。其组织之庞大,地域之广大,声势之浩大,战斗力之强大,在电白的红卫兵组织中无与伦比。半年后因中央有“就地闹革命“的指示,外地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便杀回了本地区。红五司只剩下本校的红卫兵,不到三百人。
六七年八月,电白和全国各地一样,搞起了派性(即由观点一致的组织联合起来,与观点不同的组织相斗),红五司的总头目、《烈火》兵团头头郑显国,准备拉红五司参加司派(当时电白一司、二司、三司、四司、电师红反司观点相同,故称为司派),但《红旗》头头陈洪星,《东文》头头肖文兴却是核派观点(当时一中有《核炸》兵团,与该组织观点相同的称为核派)而坚决反对。因此,《红旗》、《东文》退出红五司,与《延安》等兵团联合,称《红旗公社》(这《红旗公社》后成为沙琅地区核派的中坚力量),形成二中的核派组织。红五司只剩下《烈火》、 《星火》一百多人,又吸收琅小《轰资击旧》、《鹰击长空》两个兵团共也一百多人,与《红闯》、《一二九》组成二中的司派。因此,二中便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组织。
两大派交锋较量的形式,主要是大辩论,先是在校园内进行,后发展为上街辩论,深入和影响社会。从白天到晚上,从不间断。以下两场较量,最为经典:
八月二十七日中午,《东文》约三十多人,在校门口截住两位路过的电司《红反司》学生进行辩论。《红反司》学生从容争辩,但寡不敌众,处于下风。辩论进行一个多钟后,核派加大力量,传来《宣革》总部二十多人(《宣革》是《延安》骨干苏彦才发展的街道核派组织)。时适学校的司派下乡活动来返,在校的郑置国采取应急措施,调来粮所《钢铁》兵团五十多工人,东方场职工近百人、沙琅大队、尚塘大队农民三百多人,进行反围攻,直辩斗到下午四点,司派反败为胜。这是沙琅地区首次核司二派的社会公开大较量,也是第一次学生活动发展到工农参与的活动。
十一月三日,学校司核的双方协定,各派出二名代表,进行辩论,时间为当月九日晚上七时开始,地点于沙琅中心台(现旧街中心商场对面),裁判及主持则由公社武装部负任,这是双方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一次极有代表性和社会性的活动。九号晚上六时许,中心台前便围满了沙琅地区的市民、工人、农民和学生,约三四千人,司核派主辩为肖衡(《红卫》兵团头目),副主辩为廖和荣(《星火》兵团头目),核派主辩原定为汪宜柏(《延安》兵团头目),副主辩为陈洪星。汪宜柏和肖衡这两位同班好友,将各事其主,以敌对的身份在几千人的大场面亮场露面,而各自肩负重任。大辩论开始时,征得裁判同意,核派副主辩陈洪星更换为一中《新一中》李XX。辩论初期,肖李舌战,平平进行。然李XX乃水东地区的辩论老将,经验老到,开始时只不露其真面目,渐渐的论据雄辩,大有后居高临下之势。而肖衡,虽言利口尖,却力不从心,渐渐招架不住。最后全无还手之功。尽管廖和荣也频频弄言,鼎力相助,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结果是核派获胜。
第二天,核派乘胜追击,从水东《核炸》中请来几部宣传车,《红旗》、《延安》、《东文》等也倾城出动,在沙琅十字街口展开声势异常浩大的宣传活动。《烈火》、《星火》在关中元、刘经超老师和职员黄继光的指导下,组织力量,进行有力的反击。粮所工人,东方场职工、尚塘大队农民共几千人,在郑显国的指挥下,团团围住对方宣传车和主辩骨干,使其喘不过气来。直到下午六时,核派几辆被困的宣传车,在苏彦才组织的《宣革》总部队员掩护下,才狼狈离开。陈洪星等人当时真不该画蛇添足。
随着全国派性活动的不断深入,二中的二大派组织已由文斗阶段进入武斗阶段,他们结束了双方每日上街辩论的形式,各自抢取了枪支弹药,占据了据点。核派以沙琅建筑工会大楼(现勇和堂大药房店址)为据点,有重机一挺、轻机三挺、冲锋枪七支、步枪十七支、手榴弹数箱。司派则以沙琅供销社大楼为据点,武器比核派多出几倍。可他们受当地组织的牵制,不比核派,有独立行动大权。二中这些昔日埋头苦读的文弱书生们,现已全副武装,即将成为浴血撕杀的“勇士”了,往时一起共窗同师的学友们,现已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了。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其时部分不愿意参加武斗的学生已返家,双方参战的人数都为百人左右。此时的《红旗公社》,原来以《红旗》为核心的核派组织,已变为以《延安》为核心了。但陈洪星仍为核派的主要领导人。而司派此时已发展为以《红闯》为核心。《红闯》头目汪土胜的领导地位,几乎代替了郑显国。由于社会力量的关系,武斗阶段,核派始终处于劣势。司派曾两次荷枪弹实攻打建筑工会的核派组织。第一次为六七年十二月,沙琅地区司派纠集了六区司派的武装力量,约五百多人进行武力攻打建筑工会。陈洪星、汪宜柏指挥二中核派力量进行奋力坚守,使司派目的落空。第二次为六八年七月,电白司派调来第一纵队(电白沿海地带)二百多人、广西联指(即广西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一千多人,加上司派的第三纵队(电白山区)三百多人,足足一个半团的浩大武装力量,以拉枯摧朽之势,围住建筑工会攻打。据点中的核派,坚守一天一夜之后,于凌晨五点,安置好重伤员,携带轻伤员,借西面未收割的稻田为掩护,安全撤离,转移黄岭。值得一提的是:核派当时的总指挥陈洪星,是一位未满十六岁的初三学生,他能镇定指挥、沉着料事,带领一百多学生,在没有一个死亡的情况下,巧妙地组织安全撤离,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事后七零八七部队政委周进修评价说:陈洪星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一个正规军的连长。另外,两次的军事活动中,二中的司派学生只有少数参与,并没有一个参加筹划和指挥。而陈洪星指挥的成功撤离,也有不足之处:《延安》崔倍,高三学生,下垌人,成为这次防卫战唯一的重伤员。陈指挥撤离前,将其转移到附近老百姓家(据说是崔很亲的亲戚),而被藏主出卖,当场被司派枪毙,这是核派学生中第二位遇难者。第一位遇难者为吴建中,《红旗》干将,初二学生,望夫人。一次夜间执行任务,于曙光场十八队路口被同伙误枪击毙,后葬于二中校园内的花墩中。武斗结束后,其家属将骸骨取走。第三位遇难者崔锡义,高二学生,下垌人,原为《红闯》成员,后退出,属其同乡人报私仇,将其捕入沙琅司派据点,活活的用木板压死。第四位遇难者钟国,高二学生,《红旗》干将,在据点中,让司派六零炮弹片射入脑后,虽作了手术医治,但留下严重后遗症,武斗结束后死亡。而司派方面,第一位遇难者肖衡,《红卫》头头,高三学生,那霍人,在攻打沙琅核派的另一个据点鱼苗场中,中弹负伤,因未能及时抢救而流血过多死亡,死后厚葬于铜鼓岭凉亭旁,武斗结束后,其家属亦将其骸骨取走。肖衡死后,司派由杨炜业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忍看朋辈成新鬼》长达三万多字的缅怀、赞扬文章,记入了肖衡文革中的典型事迹。此文在双方学生中都引起很大的反应,一时被称为“派性文学”的经典之作。
震撼全省的沙琅战役中,二中司派四人遇难,其中汪锦辉,初三学生,《星火》成员,观珠人,守供销大楼时中弹,一小时后死亡;吴祠林,初二学生,《星火》干将,沙琅人,亦在防守中中弹身亡;谢斌,观珠人,高三学生,《欧阳海》头头,战役近尾声时,出逃中于二中背中弹倒下,无人抢救,约两个多小时后死亡;廖和荣,《星火》头头,《红五司》主骨干,沙琅失守后被俘,由核派拉上铜鼓岭枪决。这九位无辜的遇难者,本正值青春年华时,却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去得冤无头、债无主,真教人心寒,愿他们地下安息,泉下有灵,保佑他们的亲人和同学平安。
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核派学生独挡一面,自主自立,虽生活清贫,然在某个角度上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得到锻炼和磨练。而在残酷的沙琅战役中,他们并不担任任何的主攻任务,只作向导。然司派学生很不如意。一方面,原五司体系与《红闯》等不和,常有小冲突;另一方面居人篱下,受人牵制,不能自立。如吴建中死后要葬于二中校园,司派学生义愤填膺,准备武装阻止,却被上头强行制止。崔锡义被捕入据点时,汪土胜(《红闯》头头)与郑显国、肖俊焕、廖和荣等人出面,进行集体营救崔锡义,上头亦不予理乎。沙琅战役前,他们又要求出守铜鼓岭,亦未得准许。
沙琅战役结束时,除郑显国出差和几位战死外,其余司派学生近百人全部被俘。经核派学生核定后,将部分头目干将押送往阳江,其余的即以“受蒙蔽无罪”释放。押往阳江的有汪土胜、肖俊焕、杨炜业、黄燕耀、杨茂青等十多位学生。值到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表后,他们才返回二中。此后,公社“革委会”成立,武斗及派性活动结束,老师、双方学生返校,随之军管小组和工宣队进驻学校,双方学生互相“斗私批修”,握手言好,解除鸿沟。初二初三、高二高三高四学生毕业离校,二中校园,阴霾渐散。
此阶段,二中相继招入新生,谢克明已进干校、冯宗钦已故。学生由工宣队领导,教务工作则由何佛根老师主持(何老师此时已改名何东)。原先毕业的学生黎振光、吴勇、郭春春等,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二中的第一代工农兵学员。七九年全国恢复高考,毕业出去多时的许植、廖美光、陈和升等及后来应届毕业的朱越广、高克勤、林辉、黄学龄等人金榜提名,足显二中实力雄厚、藏龙卧虎。
八十年代后,因电白体制改革,教学重点转移,二中已由重点中学改为面点中学,学校走向斜坡。昔日二中校长谢克明、教师陈作达,前后分别任电白教育局的正副局长。原二中老师梁卓华、崔南屏、庞桂秋、谢强等,分别任一中、电海中学、水东中学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刘经超任局教研室主任,其余老师皆于重点中学任骨干老师。
此后,二中好几任校长,在新的体制下,都心有余力不足,未能使二中重显文革前的雄风。然己丑虎岁,二中有幸,新任校长陈国权,很有改革才能和冲劲,仅一年内,便使二中生机盎然。往日的校友和山区人民,都在拭目以待,期盼二中振兴腾飞,还回与电白一中并排的本来面目。
后记:
笔者也曾在那暴风雨的日子里摇旗呐喊,现回想起来,唯觉幼稚而已。然那毕竟是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经历,想忘却它,忘却那昔日的同伴和事物,让它像一场梦。但它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梦,况且梦醒后人们尚会去寻味。本想不加评论地如实地记下它,但四十多年的记忆难免是朦胧的。也曾想与那往日的同伴们聚一聚、聊一聊,把那些断碎了的记忆缀连起来、把那些淡薄了的情感加热起来,把那些朦胧的经历清晰起来。但这不同于退伍兵们的战友聚集,也不等于那同窗们的同学聚会,毕竟是不光彩的岁月和经历,那些在生命与血的付出中结下的情谊,也只能深深地默默地埋在心中。故此,笔者年老孤零而迟钝的回忆,本文中事件的出入与差错,也就难免,在此敬请诸位师兄师弟们见谅和斧正。文中所提及的人物,皆未经许可,笔者的冒昧之处,更望包涵见谅。
十年动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电白县第二中学风雨飘摇,伤痕累累。笔者记下它的遭遇,意在让昔日同窗、日后的学棣,牢记住这历史的创伤。
那时的二中,从规模、师资、设备皆与电白一中相等,是电白仅有的两所完中之一,生源主要源于麻岗、大衙、林头、羊角、下垌、黄岭、观珠、沙琅、罗坑、那霍、望夫一带。六一年前为九个班(即初中每级二班、高中每级一班)、六二年后高中不变,初中增收两个班。到六四年,二中便成为初中十二个班。共高中十五个班,约七百多人的学校。这段时间,学校的教师约四十人多人,职员六人,校长谢克明、教导主任冯宗钦、工会主席李德发。
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后,二中便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文革浪潮之中。先是成立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文革的任务是领导和组织开展运动。如发展红卫兵、破四旧(旧文化、旧风俗、旧思想、旧习惯)、大字报上街。此外,文革的任务还要在教师中定下黑帮分子、选送六次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名单。文革的成员是由县委工作组指定的部分出身好的学生。他们代表了当时学校的最高权力。七月,暑假将至时,全校学生卷入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的热流。他们一般是以班为单位。多则七八十人,少则十多人,步行全国各地,大部分到广州,个别人到北京。约近百人到了毛主席的故乡湖南韶山。九月,大串连结束。全校同学返校闹革命。学生们把各地的经验带回学校。于是,学生们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一般称为战斗兵团或造反大队。如高四(当时高考停止招生,他们毕业后返校闹革命)为“烈火“战斗兵团、高三为”延安“战斗兵团、高二为”红闯“战斗兵团。高一为”一二•九“造反队、初三、初一为”红旗“战斗兵团、初二则有”东风“、”文锋“、”星火“等战斗兵团。此外,还有跨班级的红卫兵组织,如”燎原“、”井冈山“、”独立“、”鲁迅“、“五四”、“红卫”、“欧阳海”、“三二一一”等。当时众多的红卫兵组织中,队伍最庞大、战斗力最强的是“红旗”兵团,“延安”、“烈火”则次之。“东风”、“文锋”联合为“东文总部”,亦是较活跃的组织之一。
当时的教师划分为三个等级,部分出身好的,如陈作达、林文锐、何佛根,刘经超、张其亦、关中元、程为东等老师,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较为自在;部分出身不够好的,不受太大的冲击。红卫兵们组织他们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劳动。如崔民佣、温和、温文让、唐济林、庞桂秋、冯宗钦、林中亚、谢盘铭、王莲秀等老师。部分出身差的却受批斗,带高帽挂牌游街,列入黑帮行列,完全失去自由,如崔南屏、李德发、高川若、刘东勃等老师。其中最惨为李德发和高川若。一段时期的批斗后,由文革开除出教师队伍,送返家乡参加生产劳动。校长谢克明也受到批斗,但冲击不大。李德发回乡后,没有旧屋居住,只好搭起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的茅屋,与其子李柯居住,后遭火灾,茅屋与简单的家具焚之一炉。好长一段时间,父子二人借居生产队的队屋里,生活过得异常艰苦。高川若厄运临头,这位大学时候参加革命,后留学德国、日本的学者,元帅聂荣臻、日本首相田中的同窗挚友,回乡后不到两个月,便被贫下中农“专政”,用锄头活活砸死,其惨不可言。这事惊震甚大,后来,周恩来、聂荣臻闻此事都十分气愤和惋惜。七一年田中访华,在北京知道消息后,即时为他默哀了三分钟。高川若的平生,后来已载入电白县县志。
红卫兵组织均受文革的领导。各自司令部(办公室)设在相应教室里,任务是组织和参加一些批斗会,写大字报,学习社论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调查搜集和揭露黑帮“罪状“等。另一个热潮是:部分学生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演出,其机构均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排练文娱节目,到各地演出。这样的组织有竟达四个之多,其中是《欧阳海》宣传队、《红卫》宣传队、《长征》宣传队、《三二一一一》宣传队。每个宣传队的节目都达三四十个,足足可演三个小时。演员、乐器水平几乎都达专业水准。他们穿州过县,频频演出。比如《欧阳海》宣传队,一个月曾巡走四个县,上演二十二晚,比当时的专业剧团演出还多。此外,还有些组织也积极参与,排练大量节目,但不外出演出,只参加当地的一些演出,如《红旗》兵团、《一二九》造反队等。这段时间,二中造就了大量文娱人才。
一段时间后,文革因执行所谓错误路线(当时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工作组长赖良到二中作检讨。学校掀起了批判文革的高潮,主要以《烈火》、《红旗》为主力。从此,文革解散,各红卫兵组织的活动不受束缚。但因文革的主要成员都在《延安》,而导致《延安》与《烈火》、《红旗》不和。
当时,学校成立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红卫兵组织,即电白县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五司令部(简称红五司,当时一中成立一司,电白供销系统成立二司,邮电、水电等系统成立三司,四司则为水东地区的工人组织)。红五司以《红旗》、《烈火》、《东文》、《星火》为核心,组织六区各镇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约两千多人。其组织之庞大,地域之广大,声势之浩大,战斗力之强大,在电白的红卫兵组织中无与伦比。半年后因中央有“就地闹革命“的指示,外地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便杀回了本地区。红五司只剩下本校的红卫兵,不到三百人。
六七年八月,电白和全国各地一样,搞起了派性(即由观点一致的组织联合起来,与观点不同的组织相斗),红五司的总头目、《烈火》兵团头头郑显国,准备拉红五司参加司派(当时电白一司、二司、三司、四司、电师红反司观点相同,故称为司派),但《红旗》头头陈洪星,《东文》头头肖文兴却是核派观点(当时一中有《核炸》兵团,与该组织观点相同的称为核派)而坚决反对。因此,《红旗》、《东文》退出红五司,与《延安》等兵团联合,称《红旗公社》(这《红旗公社》后成为沙琅地区核派的中坚力量),形成二中的核派组织。红五司只剩下《烈火》、 《星火》一百多人,又吸收琅小《轰资击旧》、《鹰击长空》两个兵团共也一百多人,与《红闯》、《一二九》组成二中的司派。因此,二中便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组织。
两大派交锋较量的形式,主要是大辩论,先是在校园内进行,后发展为上街辩论,深入和影响社会。从白天到晚上,从不间断。以下两场较量,最为经典:
八月二十七日中午,《东文》约三十多人,在校门口截住两位路过的电司《红反司》学生进行辩论。《红反司》学生从容争辩,但寡不敌众,处于下风。辩论进行一个多钟后,核派加大力量,传来《宣革》总部二十多人(《宣革》是《延安》骨干苏彦才发展的街道核派组织)。时适学校的司派下乡活动来返,在校的郑置国采取应急措施,调来粮所《钢铁》兵团五十多工人,东方场职工近百人、沙琅大队、尚塘大队农民三百多人,进行反围攻,直辩斗到下午四点,司派反败为胜。这是沙琅地区首次核司二派的社会公开大较量,也是第一次学生活动发展到工农参与的活动。
十一月三日,学校司核的双方协定,各派出二名代表,进行辩论,时间为当月九日晚上七时开始,地点于沙琅中心台(现旧街中心商场对面),裁判及主持则由公社武装部负任,这是双方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一次极有代表性和社会性的活动。九号晚上六时许,中心台前便围满了沙琅地区的市民、工人、农民和学生,约三四千人,司核派主辩为肖衡(《红卫》兵团头目),副主辩为廖和荣(《星火》兵团头目),核派主辩原定为汪宜柏(《延安》兵团头目),副主辩为陈洪星。汪宜柏和肖衡这两位同班好友,将各事其主,以敌对的身份在几千人的大场面亮场露面,而各自肩负重任。大辩论开始时,征得裁判同意,核派副主辩陈洪星更换为一中《新一中》李XX。辩论初期,肖李舌战,平平进行。然李XX乃水东地区的辩论老将,经验老到,开始时只不露其真面目,渐渐的论据雄辩,大有后居高临下之势。而肖衡,虽言利口尖,却力不从心,渐渐招架不住。最后全无还手之功。尽管廖和荣也频频弄言,鼎力相助,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结果是核派获胜。
第二天,核派乘胜追击,从水东《核炸》中请来几部宣传车,《红旗》、《延安》、《东文》等也倾城出动,在沙琅十字街口展开声势异常浩大的宣传活动。《烈火》、《星火》在关中元、刘经超老师和职员黄继光的指导下,组织力量,进行有力的反击。粮所工人,东方场职工、尚塘大队农民共几千人,在郑显国的指挥下,团团围住对方宣传车和主辩骨干,使其喘不过气来。直到下午六时,核派几辆被困的宣传车,在苏彦才组织的《宣革》总部队员掩护下,才狼狈离开。陈洪星等人当时真不该画蛇添足。
随着全国派性活动的不断深入,二中的二大派组织已由文斗阶段进入武斗阶段,他们结束了双方每日上街辩论的形式,各自抢取了枪支弹药,占据了据点。核派以沙琅建筑工会大楼(现勇和堂大药房店址)为据点,有重机一挺、轻机三挺、冲锋枪七支、步枪十七支、手榴弹数箱。司派则以沙琅供销社大楼为据点,武器比核派多出几倍。可他们受当地组织的牵制,不比核派,有独立行动大权。二中这些昔日埋头苦读的文弱书生们,现已全副武装,即将成为浴血撕杀的“勇士”了,往时一起共窗同师的学友们,现已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了。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其时部分不愿意参加武斗的学生已返家,双方参战的人数都为百人左右。此时的《红旗公社》,原来以《红旗》为核心的核派组织,已变为以《延安》为核心了。但陈洪星仍为核派的主要领导人。而司派此时已发展为以《红闯》为核心。《红闯》头目汪土胜的领导地位,几乎代替了郑显国。由于社会力量的关系,武斗阶段,核派始终处于劣势。司派曾两次荷枪弹实攻打建筑工会的核派组织。第一次为六七年十二月,沙琅地区司派纠集了六区司派的武装力量,约五百多人进行武力攻打建筑工会。陈洪星、汪宜柏指挥二中核派力量进行奋力坚守,使司派目的落空。第二次为六八年七月,电白司派调来第一纵队(电白沿海地带)二百多人、广西联指(即广西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一千多人,加上司派的第三纵队(电白山区)三百多人,足足一个半团的浩大武装力量,以拉枯摧朽之势,围住建筑工会攻打。据点中的核派,坚守一天一夜之后,于凌晨五点,安置好重伤员,携带轻伤员,借西面未收割的稻田为掩护,安全撤离,转移黄岭。值得一提的是:核派当时的总指挥陈洪星,是一位未满十六岁的初三学生,他能镇定指挥、沉着料事,带领一百多学生,在没有一个死亡的情况下,巧妙地组织安全撤离,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事后七零八七部队政委周进修评价说:陈洪星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过一个正规军的连长。另外,两次的军事活动中,二中的司派学生只有少数参与,并没有一个参加筹划和指挥。而陈洪星指挥的成功撤离,也有不足之处:《延安》崔倍,高三学生,下垌人,成为这次防卫战唯一的重伤员。陈指挥撤离前,将其转移到附近老百姓家(据说是崔很亲的亲戚),而被藏主出卖,当场被司派枪毙,这是核派学生中第二位遇难者。第一位遇难者为吴建中,《红旗》干将,初二学生,望夫人。一次夜间执行任务,于曙光场十八队路口被同伙误枪击毙,后葬于二中校园内的花墩中。武斗结束后,其家属将骸骨取走。第三位遇难者崔锡义,高二学生,下垌人,原为《红闯》成员,后退出,属其同乡人报私仇,将其捕入沙琅司派据点,活活的用木板压死。第四位遇难者钟国,高二学生,《红旗》干将,在据点中,让司派六零炮弹片射入脑后,虽作了手术医治,但留下严重后遗症,武斗结束后死亡。而司派方面,第一位遇难者肖衡,《红卫》头头,高三学生,那霍人,在攻打沙琅核派的另一个据点鱼苗场中,中弹负伤,因未能及时抢救而流血过多死亡,死后厚葬于铜鼓岭凉亭旁,武斗结束后,其家属亦将其骸骨取走。肖衡死后,司派由杨炜业执笔,写了一篇题为《忍看朋辈成新鬼》长达三万多字的缅怀、赞扬文章,记入了肖衡文革中的典型事迹。此文在双方学生中都引起很大的反应,一时被称为“派性文学”的经典之作。
震撼全省的沙琅战役中,二中司派四人遇难,其中汪锦辉,初三学生,《星火》成员,观珠人,守供销大楼时中弹,一小时后死亡;吴祠林,初二学生,《星火》干将,沙琅人,亦在防守中中弹身亡;谢斌,观珠人,高三学生,《欧阳海》头头,战役近尾声时,出逃中于二中背中弹倒下,无人抢救,约两个多小时后死亡;廖和荣,《星火》头头,《红五司》主骨干,沙琅失守后被俘,由核派拉上铜鼓岭枪决。这九位无辜的遇难者,本正值青春年华时,却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这样去得冤无头、债无主,真教人心寒,愿他们地下安息,泉下有灵,保佑他们的亲人和同学平安。
在整个武斗过程中,核派学生独挡一面,自主自立,虽生活清贫,然在某个角度上说,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得到锻炼和磨练。而在残酷的沙琅战役中,他们并不担任任何的主攻任务,只作向导。然司派学生很不如意。一方面,原五司体系与《红闯》等不和,常有小冲突;另一方面居人篱下,受人牵制,不能自立。如吴建中死后要葬于二中校园,司派学生义愤填膺,准备武装阻止,却被上头强行制止。崔锡义被捕入据点时,汪土胜(《红闯》头头)与郑显国、肖俊焕、廖和荣等人出面,进行集体营救崔锡义,上头亦不予理乎。沙琅战役前,他们又要求出守铜鼓岭,亦未得准许。
沙琅战役结束时,除郑显国出差和几位战死外,其余司派学生近百人全部被俘。经核派学生核定后,将部分头目干将押送往阳江,其余的即以“受蒙蔽无罪”释放。押往阳江的有汪土胜、肖俊焕、杨炜业、黄燕耀、杨茂青等十多位学生。值到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表后,他们才返回二中。此后,公社“革委会”成立,武斗及派性活动结束,老师、双方学生返校,随之军管小组和工宣队进驻学校,双方学生互相“斗私批修”,握手言好,解除鸿沟。初二初三、高二高三高四学生毕业离校,二中校园,阴霾渐散。
此阶段,二中相继招入新生,谢克明已进干校、冯宗钦已故。学生由工宣队领导,教务工作则由何佛根老师主持(何老师此时已改名何东)。原先毕业的学生黎振光、吴勇、郭春春等,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二中的第一代工农兵学员。七九年全国恢复高考,毕业出去多时的许植、廖美光、陈和升等及后来应届毕业的朱越广、高克勤、林辉、黄学龄等人金榜提名,足显二中实力雄厚、藏龙卧虎。
八十年代后,因电白体制改革,教学重点转移,二中已由重点中学改为面点中学,学校走向斜坡。昔日二中校长谢克明、教师陈作达,前后分别任电白教育局的正副局长。原二中老师梁卓华、崔南屏、庞桂秋、谢强等,分别任一中、电海中学、水东中学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刘经超任局教研室主任,其余老师皆于重点中学任骨干老师。
此后,二中好几任校长,在新的体制下,都心有余力不足,未能使二中重显文革前的雄风。然己丑虎岁,二中有幸,新任校长陈国权,很有改革才能和冲劲,仅一年内,便使二中生机盎然。往日的校友和山区人民,都在拭目以待,期盼二中振兴腾飞,还回与电白一中并排的本来面目。
后记:
笔者也曾在那暴风雨的日子里摇旗呐喊,现回想起来,唯觉幼稚而已。然那毕竟是人生路上的一次重要经历,想忘却它,忘却那昔日的同伴和事物,让它像一场梦。但它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梦,况且梦醒后人们尚会去寻味。本想不加评论地如实地记下它,但四十多年的记忆难免是朦胧的。也曾想与那往日的同伴们聚一聚、聊一聊,把那些断碎了的记忆缀连起来、把那些淡薄了的情感加热起来,把那些朦胧的经历清晰起来。但这不同于退伍兵们的战友聚集,也不等于那同窗们的同学聚会,毕竟是不光彩的岁月和经历,那些在生命与血的付出中结下的情谊,也只能深深地默默地埋在心中。故此,笔者年老孤零而迟钝的回忆,本文中事件的出入与差错,也就难免,在此敬请诸位师兄师弟们见谅和斧正。文中所提及的人物,皆未经许可,笔者的冒昧之处,更望包涵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