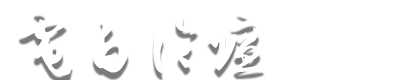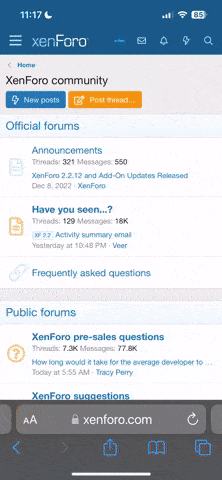- 注册
- 2004-10-02
- 帖子
- 1,977
- 反馈评分
- 1
- 点数
- 61
“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幻想在中国的破灭,魔鬼已经释放出来,对魔鬼的抗议也已经释放出来,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分化、对峙和制衡局面已经公开化,笼罩天地的意识形态迷雾已经消散,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的交手过程已经开始,中国的历史又到了一个景致异常清晰的新起点。
不是出现了极度的不和谐,绝不会如此高调提出“和谐社会”。这不和谐正是那曾被描述得梦幻般的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这个梦幻已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因此被搅得面目全非。现实已经犹如噩梦:阶级分化极深,利益争夺势如水火。强势集团已经狰狞毕露,民众的反抗日益激化,思想界大分裂,互相攻伐,互不相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巨大而深刻的分裂,这是中国决定性的损失,是新中国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演变的总结果,在此时提出“和谐社会”可谓意味深长。中国政治不得不走向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决定性地输掉,它现在只能靠权力的强制维持,这是绝妙的讽刺,宣扬自由的自由主义居然只能紧抱强权。这表明,自由主义者只剩下对既得权势和利益的现实意识,贪婪已经不加掩饰。各阶层也都日益明确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共同富裕”人人嗤之以鼻,幻想已抛弃,战斗已开始,各种武器已捡起。
基于阶级利益分析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决定性地不可抑制地复兴,左派力量迅猛增长,各种因素都在推动着它,道义和民心的力量逐渐归于左派。而右派则盘踞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是当今中国最显著的力量格局,左派的力量是深厚的、广泛的潜力无穷的,右派的力量是现成的强硬的雄厚的,这两种力量的深刻对峙,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危机。
中央政府左右为难,绝不敢轻易地单方面倾向哪一方,这种两难导致了现实主义,“和谐社会”由此提出,中央政府由此捡起一项内涵宽泛而复杂的政治使命,希图挣脱左右争斗之旋涡,并以左右逢源,中央正是个中间派,其理论系统化必然是国家主义。这就是当今中国左、右、中三派之政治格局。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格局。中央的“和谐”主义是不主张争论的,是抑制过激争论的,但又是不可能禁止争论的,是调和派、制衡派,甚而是综合派。中央不会主动加入争论,但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左右争斗的战局所裹挟(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是典型事例)。而左右两派都将日益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不参战”的中央竟会成为左右两派的争夺对象,如果中央也更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顺势地更加具有开明精神和容纳能力,则三方的互动可能会意想不到地演进为不定制的“两派制”民主政制。于是“和谐社会”的政治运转将是中央政治容纳左右争论,又抑制争论的过激,同时又吸取争论的成果,既不禁止,也不放纵,还要自觉吸取和引导。
超脱了左右之争,中央将腾出手来竭力营造国家的整体感,树立国家利益为左右两派都不容争论的根本准则,如此,民族主义必被赋予巨大的政治正确性,进而又将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因此,是否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共产党将变成“共和”党,致力于国家的整合与强大,而真正的共产党的社会使命则将由左派去促进和完成?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这将会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并且,一个长远的趋势可能是,共产党在保持国家“共和”的情况下,将会日益倾向于左派,最终实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在此过程与格局下,左派实际上承担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专职的先锋队,而作为执政者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在承担基本的现实主义统治职能的情况下作为左派的盟友。这两者的分化、分工和配合将是微妙的(这种分工可能对执政党和左派都是一种解放),并且这可能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稳健而富有弹性的方式。
右派则在此过程中可以作为责任承担者,也就是共产党政策失误的“替罪羊”,中共中央因超脱左右之争而始终握有了无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国家在法理上始终不承担错误,始终避免全局性的国家认同危机,共产党将可能日益抽象、同化为中国国家之象征(以一个不讨好的例子而言,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巧妙地躲避了二战罪责,因而维持了日本高度的国家认同)。共产党将以此磨练新的政治智慧。
可以肯定,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导致右派有一个长久的退却期,现存的一切与国家主义原则直接抵触的极右主义都将受到有力抑制,中央还将借助左派的力量抑制右派。即就左右之争而言,只要中央不过分压抑左派,则右派必然遭遇惨败(04年的国企争论同样是典型),因为左派积蓄已久已深。更广泛的多的民族主义也将其矛头直指右派(近日的反日运动就是如此),民族主义又是左派的同盟军和后备军。所以,右派四面受敌,陷入千夫所指。但是,多年改革的即定“成果”实际上又在支撑着右派,使之居于正统和主流的地位,而左派是在一个长长的退却期之后才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其所掌握的现实资源是相当微薄的,并且本身也是处境尴尬,是处于在野的边缘的地位。当然同一份改革的成果也在支撑着左派,如果其支撑右派的是“即得的权势和利益”,那么民众对“即得的权势和利益”的猖獗罪恶的愤怒,也导致民众支撑着左派的信条。但是,民众的支持大部分还是潜在的,而且民众的力量本身又早已被自由主义所拆散和瓦解,这一点将在正反两方面决定左派的前途。第一,左派的前途是极其深远的,只要将潜在的民众力量变为现实的力量。第二,道路又将是艰难的,因为要真正发动民众的力量从来是最大的政治难题。左右两派将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但结局也将更加彻底。
说白了,“和谐社会”的提出从反面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承认了左右两派的对峙格局,政治力量的多元化格局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前景,中央将不再支持右派的单方面垄断,那么解除这种垄断,这实际上就是给左派机会,提出“和谐社会”其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这一点,而其自身内容却已经不重要。
中央肯定不会以明确的姿态左转,这甚至不是中央的职责,而正是要靠左派自己去把握这个机会,填充自己的力量,显示自己的才能,顺理成章地推动大局的左转,中央当然不会阻挠这种顺理成章的左转,而会顺水推舟,或者因势利导。中央已经不是邓江时代的中央,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中央,而是全新的中央,这个中央是作为多元政治力量中的一元,作为镇定国家大局中轴转纽,它亦实亦虚,而新中国的前途将前所未有地取决于左右两种力量的斗争,而不再是中枢力量的“设计”,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出现一个全新的格局和前景,也许这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左派应该看清这一点,看清自己的机会,和自己应该做的事,并决定自己的策略。但中央政治决不应该趋向于软弱,这正是何新提出“新国家主义”的主旨。客观上,中央政治可以是左右之争的消极的中和与综合,但是,主观上,中央政治又必须是这种中和与综合的自觉,最终积极地驾御左右之争,而不是单纯被左右之争所左右。因此,中央政治需要坚强的力量。
“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但是政治格局的转折,更深远的是政治精神的转折。之前提出的“小康”社会,主要是一个以单纯的经济生活指标衡量的社会,“小康”就是指一种经济生活水平。但“和谐社会”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它包含了显著的政治秩序的内容。“小康”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的必然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从其前过激的政治气氛中退却,同时也就必是自由主义一路高涨的时代,自由主义是对政治原则的最强有力的瓦解,也是对自发经济力量的最高效的释放,于是自由资本主义狂飙突进,这又造成社会的急剧分化,直到危及国家稳定的根基。“和谐社会”的提出预示着政治精神的苏醒,形势没有选择,统治者没有选择,但是一旦做出选择又必须不是搁于被动,而必须是应于主动。
何新提出的“新国家主义”正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选择,其现实主义绝不是消极地承认现实,而是面对现实的政治自觉,即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指针指导社会运行。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精神实际上必将被无形地扭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纯经济主义必须首先服从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实际上,“经济”与“利益”是有深刻差别的,若“经济”只是财富,则“利益”还必须牵扯到财富的归属和分配,牵扯到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也就必然进入政治范围。单纯的经济建设决不可能达到一个“和谐社会”,再也不可能让一切力量都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了。
“和谐社会”的底盘是“国家主义”,国家要刚强,社会要温柔,“和谐社会”需要“国家主义”的支撑,“国家主义”需要“和谐社会”的呵护,而这一切又正是中央政治需要捏拿和把握的。这是两柄剑,一刚一柔,要寓刚于柔,又以刚护柔,一隐一显,“国家主义”隐,而“和谐社会”显。中央的任务就是以“国家主义”支撑大局,以“和谐社会”探索以引领方向。
不是出现了极度的不和谐,绝不会如此高调提出“和谐社会”。这不和谐正是那曾被描述得梦幻般的自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这个梦幻已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中国的社会现实也因此被搅得面目全非。现实已经犹如噩梦:阶级分化极深,利益争夺势如水火。强势集团已经狰狞毕露,民众的反抗日益激化,思想界大分裂,互相攻伐,互不相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巨大而深刻的分裂,这是中国决定性的损失,是新中国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演变的总结果,在此时提出“和谐社会”可谓意味深长。中国政治不得不走向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决定性地输掉,它现在只能靠权力的强制维持,这是绝妙的讽刺,宣扬自由的自由主义居然只能紧抱强权。这表明,自由主义者只剩下对既得权势和利益的现实意识,贪婪已经不加掩饰。各阶层也都日益明确了自己的现实利益,“共同富裕”人人嗤之以鼻,幻想已抛弃,战斗已开始,各种武器已捡起。
基于阶级利益分析的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决定性地不可抑制地复兴,左派力量迅猛增长,各种因素都在推动着它,道义和民心的力量逐渐归于左派。而右派则盘踞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是当今中国最显著的力量格局,左派的力量是深厚的、广泛的潜力无穷的,右派的力量是现成的强硬的雄厚的,这两种力量的深刻对峙,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政治、社会危机。
中央政府左右为难,绝不敢轻易地单方面倾向哪一方,这种两难导致了现实主义,“和谐社会”由此提出,中央政府由此捡起一项内涵宽泛而复杂的政治使命,希图挣脱左右争斗之旋涡,并以左右逢源,中央正是个中间派,其理论系统化必然是国家主义。这就是当今中国左、右、中三派之政治格局。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政治格局。中央的“和谐”主义是不主张争论的,是抑制过激争论的,但又是不可能禁止争论的,是调和派、制衡派,甚而是综合派。中央不会主动加入争论,但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左右争斗的战局所裹挟(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是典型事例)。而左右两派都将日益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不参战”的中央竟会成为左右两派的争夺对象,如果中央也更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顺势地更加具有开明精神和容纳能力,则三方的互动可能会意想不到地演进为不定制的“两派制”民主政制。于是“和谐社会”的政治运转将是中央政治容纳左右争论,又抑制争论的过激,同时又吸取争论的成果,既不禁止,也不放纵,还要自觉吸取和引导。
超脱了左右之争,中央将腾出手来竭力营造国家的整体感,树立国家利益为左右两派都不容争论的根本准则,如此,民族主义必被赋予巨大的政治正确性,进而又将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因此,是否可以下这样一个判断:共产党将变成“共和”党,致力于国家的整合与强大,而真正的共产党的社会使命则将由左派去促进和完成?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这将会成为一个明显的事实。并且,一个长远的趋势可能是,共产党在保持国家“共和”的情况下,将会日益倾向于左派,最终实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在此过程与格局下,左派实际上承担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专职的先锋队,而作为执政者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在承担基本的现实主义统治职能的情况下作为左派的盟友。这两者的分化、分工和配合将是微妙的(这种分工可能对执政党和左派都是一种解放),并且这可能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稳健而富有弹性的方式。
右派则在此过程中可以作为责任承担者,也就是共产党政策失误的“替罪羊”,中共中央因超脱左右之争而始终握有了无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国家在法理上始终不承担错误,始终避免全局性的国家认同危机,共产党将可能日益抽象、同化为中国国家之象征(以一个不讨好的例子而言,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巧妙地躲避了二战罪责,因而维持了日本高度的国家认同)。共产党将以此磨练新的政治智慧。
可以肯定,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导致右派有一个长久的退却期,现存的一切与国家主义原则直接抵触的极右主义都将受到有力抑制,中央还将借助左派的力量抑制右派。即就左右之争而言,只要中央不过分压抑左派,则右派必然遭遇惨败(04年的国企争论同样是典型),因为左派积蓄已久已深。更广泛的多的民族主义也将其矛头直指右派(近日的反日运动就是如此),民族主义又是左派的同盟军和后备军。所以,右派四面受敌,陷入千夫所指。但是,多年改革的即定“成果”实际上又在支撑着右派,使之居于正统和主流的地位,而左派是在一个长长的退却期之后才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其所掌握的现实资源是相当微薄的,并且本身也是处境尴尬,是处于在野的边缘的地位。当然同一份改革的成果也在支撑着左派,如果其支撑右派的是“即得的权势和利益”,那么民众对“即得的权势和利益”的猖獗罪恶的愤怒,也导致民众支撑着左派的信条。但是,民众的支持大部分还是潜在的,而且民众的力量本身又早已被自由主义所拆散和瓦解,这一点将在正反两方面决定左派的前途。第一,左派的前途是极其深远的,只要将潜在的民众力量变为现实的力量。第二,道路又将是艰难的,因为要真正发动民众的力量从来是最大的政治难题。左右两派将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但结局也将更加彻底。
说白了,“和谐社会”的提出从反面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承认了左右两派的对峙格局,政治力量的多元化格局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前景,中央将不再支持右派的单方面垄断,那么解除这种垄断,这实际上就是给左派机会,提出“和谐社会”其最重要的意义正在于这一点,而其自身内容却已经不重要。
中央肯定不会以明确的姿态左转,这甚至不是中央的职责,而正是要靠左派自己去把握这个机会,填充自己的力量,显示自己的才能,顺理成章地推动大局的左转,中央当然不会阻挠这种顺理成章的左转,而会顺水推舟,或者因势利导。中央已经不是邓江时代的中央,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中央,而是全新的中央,这个中央是作为多元政治力量中的一元,作为镇定国家大局中轴转纽,它亦实亦虚,而新中国的前途将前所未有地取决于左右两种力量的斗争,而不再是中枢力量的“设计”,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出现一个全新的格局和前景,也许这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左派应该看清这一点,看清自己的机会,和自己应该做的事,并决定自己的策略。但中央政治决不应该趋向于软弱,这正是何新提出“新国家主义”的主旨。客观上,中央政治可以是左右之争的消极的中和与综合,但是,主观上,中央政治又必须是这种中和与综合的自觉,最终积极地驾御左右之争,而不是单纯被左右之争所左右。因此,中央政治需要坚强的力量。
“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但是政治格局的转折,更深远的是政治精神的转折。之前提出的“小康”社会,主要是一个以单纯的经济生活指标衡量的社会,“小康”就是指一种经济生活水平。但“和谐社会”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指标,它包含了显著的政治秩序的内容。“小康”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的必然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从其前过激的政治气氛中退却,同时也就必是自由主义一路高涨的时代,自由主义是对政治原则的最强有力的瓦解,也是对自发经济力量的最高效的释放,于是自由资本主义狂飙突进,这又造成社会的急剧分化,直到危及国家稳定的根基。“和谐社会”的提出预示着政治精神的苏醒,形势没有选择,统治者没有选择,但是一旦做出选择又必须不是搁于被动,而必须是应于主动。
何新提出的“新国家主义”正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选择,其现实主义绝不是消极地承认现实,而是面对现实的政治自觉,即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指针指导社会运行。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精神实际上必将被无形地扭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纯经济主义必须首先服从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政治原则。实际上,“经济”与“利益”是有深刻差别的,若“经济”只是财富,则“利益”还必须牵扯到财富的归属和分配,牵扯到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也就必然进入政治范围。单纯的经济建设决不可能达到一个“和谐社会”,再也不可能让一切力量都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了。
“和谐社会”的底盘是“国家主义”,国家要刚强,社会要温柔,“和谐社会”需要“国家主义”的支撑,“国家主义”需要“和谐社会”的呵护,而这一切又正是中央政治需要捏拿和把握的。这是两柄剑,一刚一柔,要寓刚于柔,又以刚护柔,一隐一显,“国家主义”隐,而“和谐社会”显。中央的任务就是以“国家主义”支撑大局,以“和谐社会”探索以引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