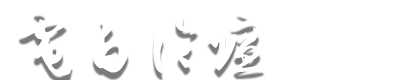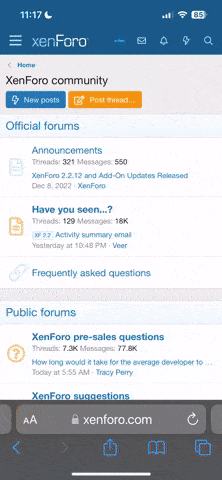-
论坛网址:https://db163.us(可微信分享)、https://0668.es、https://0668.cc(全加密访问)
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孙悟空后传 (3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叁0如狼
- 开始时间
- 注册
- 2007-04-22
- 帖子
- 5,300
- 反馈评分
- 2
- 点数
- 0
但他还未敢有甚么动作,毕竟到现在为止,他连这女子是人是鬼都不知道,他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未说过。
但一个人如果要行运了,就算走路都能踢到金子的,就算你是一只癞蛤蟆,天鹅也会飞到你嘴边,而且你想不吃还不行。秦烩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但如果平时有人恭维他说,他的运气好到了如此地步,他还不至于会去相信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已不到他不相信,原来自己的运气真的好得如此难以想象。
因为这时,他的身体忽然被一具香艳的胴体抱了个贴实,一把甜腻腻的声音,贴着他的耳根传来:“相爷,奴家真冷哦,你就真的如此忍心,不给点温暖给奴家吗?”
原来这时,这神秘女O已整个倒进了秦烩怀中,她说话时,秦烩只觉她胸前轻纱下的那对妙物,不停的在自己身上摩挲,那感觉就如孙悟空吃了人参果,全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不舒服。
此情此景,就算是柳下惠,相信都很难坐怀不乱了,何况秦烩根本就是个老淫棍,就算现他抱的是个女鬼,他也宁愿死在石榴裙下了。因为这时,他不但耳根痒痒的,内心更是痒到了极点。自然而然地,他做出了正常男人都会做的事。
那一晚,也许是秦烩今生过得最快乐最销魂的一晚了,有诗有证: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上下CD,其乐无穷!
但一个人如果要行运了,就算走路都能踢到金子的,就算你是一只癞蛤蟆,天鹅也会飞到你嘴边,而且你想不吃还不行。秦烩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但如果平时有人恭维他说,他的运气好到了如此地步,他还不至于会去相信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已不到他不相信,原来自己的运气真的好得如此难以想象。
因为这时,他的身体忽然被一具香艳的胴体抱了个贴实,一把甜腻腻的声音,贴着他的耳根传来:“相爷,奴家真冷哦,你就真的如此忍心,不给点温暖给奴家吗?”
原来这时,这神秘女O已整个倒进了秦烩怀中,她说话时,秦烩只觉她胸前轻纱下的那对妙物,不停的在自己身上摩挲,那感觉就如孙悟空吃了人参果,全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不舒服。
此情此景,就算是柳下惠,相信都很难坐怀不乱了,何况秦烩根本就是个老淫棍,就算现他抱的是个女鬼,他也宁愿死在石榴裙下了。因为这时,他不但耳根痒痒的,内心更是痒到了极点。自然而然地,他做出了正常男人都会做的事。
那一晚,也许是秦烩今生过得最快乐最销魂的一晚了,有诗有证: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上下CD,其乐无穷!
- 注册
- 2007-04-22
- 帖子
- 5,300
- 反馈评分
- 2
- 点数
- 0
第二天早晨,当秦烩醒来时,太阳已晒到了屁股,昨晚跟他一晚缠绵的美女不知何时已悄悄走了。满室却还残留着她独有的体香,这让秦烩确信,昨晚发生的事并不是一场梦。虽然这梦也太香艳太不真实了点。
秦烩却不由回忆了一番,直到这室内那美女所留异香消散殆尽,方有点不情愿的起了床,刚梳洗完毕,门外忽然进来一下人打扮的汉子,道杀皇下午请他吃午宴。。。那汉子表面虽装作恭谨,却怎能瞒过秦烩这等一向善于察言观色之人,这汉子说话当儿,眼神满是恼怒及醋意。
秦烩倒也不蠢,隐约似猜到这汉子为何有此等神色,但心下终是有点忐忑,不知杀皇何故要请他吃饭,这还是他出使鹅国以来的第一次,也不知是不是鸿门宴来的?
但他现时人在屋檐下,又那到他不答应,何况别人只是请他吃饭,他如果这样都不敢去,那不是徒让人笑话而已。他左右思量之下,还是决定赴约,因为他现在也只能见步行步,相机行事了。
秦烩却不由回忆了一番,直到这室内那美女所留异香消散殆尽,方有点不情愿的起了床,刚梳洗完毕,门外忽然进来一下人打扮的汉子,道杀皇下午请他吃午宴。。。那汉子表面虽装作恭谨,却怎能瞒过秦烩这等一向善于察言观色之人,这汉子说话当儿,眼神满是恼怒及醋意。
秦烩倒也不蠢,隐约似猜到这汉子为何有此等神色,但心下终是有点忐忑,不知杀皇何故要请他吃饭,这还是他出使鹅国以来的第一次,也不知是不是鸿门宴来的?
但他现时人在屋檐下,又那到他不答应,何况别人只是请他吃饭,他如果这样都不敢去,那不是徒让人笑话而已。他左右思量之下,还是决定赴约,因为他现在也只能见步行步,相机行事了。
- 注册
- 2007-04-22
- 帖子
- 5,300
- 反馈评分
- 2
- 点数
- 0
一路之上,秦烩所见鹅人,果然表情眼色都跟那个叫他赴宴的汉子无异,秦烩心中不免有点得意,想来昨晚那美女应是该国绝色,要不这些汉子今天看他的眼神,怎么个个都似打翻了醋坛子般。
得意之余,他却又不免有点担心,因为他知道,鹅人最是强横排外,该国有个著名的民族主义组织叫“光头党”,他们的口号就是“鹅螺丝是鹅螺丝人的鹅螺丝”,专以袭击、杀害外族人为乐,甚至不必理由,如此蛮横排外的民族可说世所罕见。
秦烩对于这些传闻,就算他以前也许还有点半信半疑,现在也信到十足矣。因为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他这一路上,已经被这些宫里的侍卫、奴仆等的眼光剁成肉渣了。
但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位看上去高大彪悍、满脸横肉、传说中杀人如麻的鹅国统帅―杀皇在席间却对他礼敬有加,不但给他夹菜夹肉,请喝最极品的伏乐加,安排了一众美丽宫女跳舞助兴,还颇为关切的问他在鹅螺丝过得适不适应,开不开心诸如此类。秦烩意料中他会提起的和约之事,他竟是绝口不提,连秦烩这种自认聪明绝顶,久练成精之人都感到有点狐疑。
但一来他今天真的是高兴,是自从他出使鹅国以来最高兴的一天。而且他昨晚精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正需要好好滋补一下。于是后来也就不作多想了,佳人美酒当前,又有如此尊贵的杀皇相陪,那是何等荣幸快乐之事哦!所以,秦烩这餐喝得很尽兴很开心,以至后来他是如何回到自己的寝室的,他都不知道了。
得意之余,他却又不免有点担心,因为他知道,鹅人最是强横排外,该国有个著名的民族主义组织叫“光头党”,他们的口号就是“鹅螺丝是鹅螺丝人的鹅螺丝”,专以袭击、杀害外族人为乐,甚至不必理由,如此蛮横排外的民族可说世所罕见。
秦烩对于这些传闻,就算他以前也许还有点半信半疑,现在也信到十足矣。因为如果眼光能杀人的话,他这一路上,已经被这些宫里的侍卫、奴仆等的眼光剁成肉渣了。
但大大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位看上去高大彪悍、满脸横肉、传说中杀人如麻的鹅国统帅―杀皇在席间却对他礼敬有加,不但给他夹菜夹肉,请喝最极品的伏乐加,安排了一众美丽宫女跳舞助兴,还颇为关切的问他在鹅螺丝过得适不适应,开不开心诸如此类。秦烩意料中他会提起的和约之事,他竟是绝口不提,连秦烩这种自认聪明绝顶,久练成精之人都感到有点狐疑。
但一来他今天真的是高兴,是自从他出使鹅国以来最高兴的一天。而且他昨晚精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正需要好好滋补一下。于是后来也就不作多想了,佳人美酒当前,又有如此尊贵的杀皇相陪,那是何等荣幸快乐之事哦!所以,秦烩这餐喝得很尽兴很开心,以至后来他是如何回到自己的寝室的,他都不知道了。
- 注册
- 2007-04-22
- 帖子
- 5,300
- 反馈评分
- 2
- 点数
- 0
此后二个星期,杀皇每天都如此好酒好肉的宴请秦烩,席间两人还交流些治国平天下之类的道理,秦烩初时纠椿苟陨被视械愕忌和戒心。但不知杀皇这招是不是摸通了中原人的习性,酒桌上谈生意,特别顺手,一年几千亿的公款吃喝就是这样吃出来滴。就更不用说吃人的口软了?
故一来二往,两人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也难怪,这两人本来就是一代奸雄,只是当初各为其族互不相识而已,但人类之间的感情是有共性的。两个星期下来,两人已混得很是稔熟,几乎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有时秦烩夜半醒来,竟颇是感慨杀皇方是明主,而中原那位混账皇帝简直就是竖子不足为谋,最大的优点就是贪图淫乐、挥霍无度。想当初秦烩身为一代南京高考状元,年青时也颇有干一番大事的理想,梦想有一天能为国家的乌托邦建设竭尽绵薄之力。
他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在私塾读书时,他的教书先生孔老头子曾问同学们长大了都想干什么?他当时就第一个举手,站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挺胸回答,“我长大了最想当秦始皇!”因为他自懂事以来最佩服的人就是秦始皇,他还记得历史上有一个叫李黑的写过首赞颂他偶像秦始皇的诗,其中的那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多么让人心潮澎湃,多么气势恢宏啊!!
不过,他的回答只换来同学们一阵讪笑,连孔老夫子都大摇其头,不以为然的教训他道:“错之哉大错也,秦王为了一已私欲杀人无数,大不仁也,要明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上众生平等,老虎如果吃不到你,你也应该割自己的一块肉给它,要不它就饿死了。。。云云。。。之乎者也。。。”
秦烩听得不禁头大,他只记得自己自从二岁时死了老爸后,他家里就多了不少野男人,每次他们来后,他母亲就必定要赶他出去,然后他就有钱买糖果吃有钱去读书了,那时他还盼着家里多来几个叔叔呢?不过自他懂点事后,在其他小朋友都叫他野种后,他终于明白了那些叔叔到他家是干什么的?
所以,他这时心里只有恨,为什么这时没有人来跟他说仁政,没人来关心过他,人穷被人欺,他认定了这道理。他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当个大人物,这样才没人再敢欺负他,没人再敢叫他为野种。
秦始皇正是他心目中这种予夺予杀的大人物。
所以,他那时做梦都想能成为象秦王那样的人。不但如此,他的梦想比秦王更大,他想成为世界之王,将全世界都统一到自己麾下,这样全世界都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了。有很多次,他已经在梦中带领将士们在多瑙河旁边洗战靴了,以至经常在梦中流着口水的笑醒。
故一来二往,两人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也难怪,这两人本来就是一代奸雄,只是当初各为其族互不相识而已,但人类之间的感情是有共性的。两个星期下来,两人已混得很是稔熟,几乎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有时秦烩夜半醒来,竟颇是感慨杀皇方是明主,而中原那位混账皇帝简直就是竖子不足为谋,最大的优点就是贪图淫乐、挥霍无度。想当初秦烩身为一代南京高考状元,年青时也颇有干一番大事的理想,梦想有一天能为国家的乌托邦建设竭尽绵薄之力。
他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在私塾读书时,他的教书先生孔老头子曾问同学们长大了都想干什么?他当时就第一个举手,站起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挺胸回答,“我长大了最想当秦始皇!”因为他自懂事以来最佩服的人就是秦始皇,他还记得历史上有一个叫李黑的写过首赞颂他偶像秦始皇的诗,其中的那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多么让人心潮澎湃,多么气势恢宏啊!!
不过,他的回答只换来同学们一阵讪笑,连孔老夫子都大摇其头,不以为然的教训他道:“错之哉大错也,秦王为了一已私欲杀人无数,大不仁也,要明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上众生平等,老虎如果吃不到你,你也应该割自己的一块肉给它,要不它就饿死了。。。云云。。。之乎者也。。。”
秦烩听得不禁头大,他只记得自己自从二岁时死了老爸后,他家里就多了不少野男人,每次他们来后,他母亲就必定要赶他出去,然后他就有钱买糖果吃有钱去读书了,那时他还盼着家里多来几个叔叔呢?不过自他懂点事后,在其他小朋友都叫他野种后,他终于明白了那些叔叔到他家是干什么的?
所以,他这时心里只有恨,为什么这时没有人来跟他说仁政,没人来关心过他,人穷被人欺,他认定了这道理。他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当个大人物,这样才没人再敢欺负他,没人再敢叫他为野种。
秦始皇正是他心目中这种予夺予杀的大人物。
所以,他那时做梦都想能成为象秦王那样的人。不但如此,他的梦想比秦王更大,他想成为世界之王,将全世界都统一到自己麾下,这样全世界都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了。有很多次,他已经在梦中带领将士们在多瑙河旁边洗战靴了,以至经常在梦中流着口水的笑醒。
- 注册
- 2005-03-27
- 帖子
- 16,013
- 反馈评分
- 1
- 点数
- 61
- 年龄
- 40
QUOTE(叁0如狼 @ 2009年09月29日 Tuesday, 12:39 PM)
呵呵,鼎鼎大名的淫民大人光临本贴,不胜荣幸!!多谢多谢。。。比起那篇“偷情”更色情是吧?

 我都喜欢
我都喜欢
QUOTE(蛙子 @ 2009年10月01日 Thursday, 11:02 AM)
故意打错字的,大作家别笑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昨晚你太早走了,可惜
呵呵,鼎鼎大名的淫民大人光临本贴,不胜荣幸!!多谢多谢。。。比起那篇“偷情”更色情是吧?
[snapback]2856549[/snapback]
QUOTE(蛙子 @ 2009年10月01日 Thursday, 11:02 AM)
故意打错字的,大作家别笑
[snapback]2857495[/snapback]
昨晚你太早走了,可惜
少年多梦,人皆如此,即使有些梦是很荒唐和很好笑的,也属正常。秦烩少时虽也象许多同龄人般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梦。但他出身寒微且命运多舛,却难得的较之一般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和现实。
从小他就明白,象他这种出身的,不比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自小家里人就已经给他们铺好了金光大道的富贵家庭子女。甚至比那些虽然贫穷但至少双亲健在、普通正常的家庭也是远比不上。因为他们的子女至少不会象他这样,自小就被人讥讽为“野种”
如果说出生于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对于秦烩来说,唯一还有点好处的话,那就是这种经历让他更早熟,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自己长大以后能出人头地,才能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并得到别人的敬畏。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读书科举一途了。所以,自小秦烩就比班上所有人读书都更努力,再加上他天生聪颖,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在17岁时就高中状元,自誉为“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当然后来有人考证,封川县文德乡(属现在封开县)出了个“岭南首魁状元”莫宣卿,高中时也只有17岁,却比秦烩迟出生了一天,他才应是“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因本文非是严肃学术论文,这里就不作甄别了。
且说秦烩高中状元后,以为这下终于时来运转,一抒抱负了。谁知皇帝除了在他状元及第那天在皇宫大殿上设宴并赐了他一杯酒后,就好象将他忘记得一干两净了一般。只让他任了个翰林院修撰的闲职,顾名思义,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干点啥的了吧?如果谁嫌自己的头发太浓密眼睛太明亮,那这份工作还算得上是不错的选择。具体点说,就是修正或考证“日暮苍山兰舟小 本无落霞缀清泉 去年叶落缘分定 死水微漾人却亡 ”之类的诗句究竟是李黑写的还是李白写的,并是否在这首诗中预言了日本去死,小泉定亡的谶语等无厘头的工作。
这还不算,这工作竟然一做还做了三十年,秦烩不但那一头浓密的热带雨林都熬成地中海了,
称呼上还多了个“三朝元老”的后缀,如果说这三十年时间里有了点成绩的话,就是在任职第28个年头的时候被现在的晕宗皇帝赐了个“内阁中书大学士”的虚衔,聊算个精神安慰吧。
“这王朝的皇帝都是些窝囊废,想不到自己堂堂一代状元,竟沦落到与鼠蚁为伴的下场,穷苦百姓培养一个人才容易吗?就这样给糟蹋了,何况自己。。。”仕途暗淡郁郁不得志,秦烩不免经常自怜自艾一番,特别是想到自己那倍加凄惨的童年时,几乎都不忍再想下去,但心中的怨气却又更添了几分。
这晚秦烩膳后正在厅里闲坐,这时忽有门僮来报,道有一旧友求见,秦烩不知是谁,挥手让门僮过去叫他进来,自已旋也整束衣冠,出去迎接。刚转过影壁,只见迎面而来的,赫然竟是小时学友,已有三十多年未见的―李中吾是也。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李中吾为何许人,其实说到他的著作,应该是市井文盲,都会略有所闻的了,不错,他就是著述有旷世奇书《厚黑学》的那个一代怪才李中吾是也。
李中吾小时跟秦烩少年同学,文采风流可谓一时瑜亮,不分轩轾。本来专心于功名的话,那一年的南京状元是他的而非秦烩的也说不定,但他偏生天生一副傲骨,为人清高自持。眼见官场腐败横行,官员贿赂成风,他一片仕途之心,不由早早的冷了下来。就在中了会元后不久,他就抛下了孔孟之书,归隐田园,醉心于研究社会百态,著书立说了。
秦烩跟他多年不见,关于他的状况也只是略有所闻。他在内心中虽对李中吾那种人生哲学不以为然,但毕竟同窗有年,且当年都是一代才子,心里不免有点惺惺相惜之心。何况两人多年不见,自己刚好今晚也满腹心事,有朋自远方来,煮酒论下英雄,不亦乐乎。于是两人略作寒暄,秦烩就命下人摆下酒席,两人下坐,不免一番觥筹交错。
几杯下肚,秦烩已有了几番酒意,今天能见旧友,心中自是高兴,但想想自己至今犹自潦倒,又是心生感触,不由长叹了口气。
李中吾正跟他喝得开心,正见他突然叹气,心下不解,讶然问道:“秦兄正喝得高兴,何故突然叹气呢?”
秦烩本是城府极深、内向寡言之人,平时心事都放心里,断不会随便跟别人提起的。但一来今天开心喝多了几杯;二来李中吾又非政界同僚,不虞酒后失言给传出去误事。最大的原因是,他现在的确是很想找个人倾诉下,难得碰到个如此适合的听众。于是在又长叹一声后,就将这些年来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股脑儿的向李中吾全倾诉了出来。
毕竟几十年的事了,即使秦烩已尽量说得简单扼要,还是花了差不多一支香的时间才好不容易说完。对秦烩来说,这可能是他平生以来,跟别人说过最多话的一次了。几乎是说得气喘吁吁、咳嗽连连,虽然说得辛苦,但将心里的苦水都倒了出来后,秦烩竟然感到心里有一种难得的舒畅感,心情好象也平和了许多。也难怪,象他这种平时做人总带着个面具,三闷棍都打不出一个响屁,除了尔虞我诈几乎没一个真心朋友的人,是很能会有这种畅尽所言的快感的。
这时秦烩拿眼光向李中吾瞧去,那眼神任谁都看得出,秦烩现在多希望从对方的口中听到些安慰及勉励的话,一个平时没什么朋友的人,也许有时内心里是特别的需要朋友的。
却见李中吾脸上似笑非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却口不作声,只是一味不停地向他劝酒,也不知他究竟有没有听清楚刚才秦烩在说什么,真是浪费了秦烩那好一番表情。
秦烩心下不乐,却又不好说什么,他本就是那种闷骚之人,这下又恢复了那种阴沉沉的的脸容,寻思。“自己真是自作多情,对牛弹琴了。”现在他只想这李中吾快点喝完酒,好结束这让他尴尬的场面。他却未想到原来自己连李中吾为何来到此地,为什么事来找他都未曾问过,只是大家一坐下就顾着向别人吐苦水。
原来这李中吾今天来找秦烩,内里却果真是有一番情由的。
且说当年李中吾归隐田园后,每日专注的,只是如何能写出本有关人性恶劣方面的专著,特别是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的发家史及统治史。人可能真是种奇怪的动物,象他这种无心于功名无心于政界发展的人,却偏偏在做学问方面对政治最感兴趣。于是在著书立说方面,也拣了这方面的主题来做。
这数十年来,他为了完成这方面的研究,那真可谓是穷经究典、呕心沥血矣。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三个月前,他那本花费了三十多年心血的巨著《厚黑学》终于问世了,这让他欣慰无比。但让他感到凄凉的是,为了写成这本书,他也将祖宗留下的,原本还算殷实的一份家产,挥霍了个一干两净。
也难怪,象他这种四肢不勤,大门不出,半年都不刮一次胡子,一年都不冲一次凉,身上那股咸鱼味连方圆五里的邻居都能闻到,除了看书就是写书的人。别人除了叫他“SB”,精神病之类,又还能叫他什么呢?更不幸的是,到李中吾大作完成时,他才仿佛发觉自己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原来祖宗留下的忒多珍玩古董。。。反正所有能给他拿来换钱的东西都早给他典当清光了。他现在除了一间茅庐和生活必需的一些台台凳凳,可说是,穷得只剩下书,因为不夸张点说,他那间烂房里几乎能塞得下的地方都塞满了书,他每次出入自己那间房子都可称得上是进行了一次体育运动。因为那书多得只能让他跳过去或侧着身慢慢地钻过去。
但李中吾现在才深切体会到,他小时候给私塾里那些教科书洗脑洗得有多厉害,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原来统统都不过是忽悠死人不包赔的歪理谬论。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那位人如其名身材高大的邓大平同志那句“实践是体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多么的正确。原来,挣钱才是硬道理,其他统统都是扯蛋。就象李中吾当时刚刚完成自己的巨著《厚黑学》时,当最初的喜极而泣过后,他发觉自己又要悲极而泣了。原来下一餐的饭钱没着落了。上天偏偏就这么捉弄人,连他想买个烧饼来庆贺数十年的心血结晶的钱竟然都没给他留下来。因为在他刚完成巨著后,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自己居然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有了。
李中吾悠悠地长叹了一口气,高呼了一声“拐伯”,很快就象变戏法一般,他那乱蓬蓬的书堆中忽然伸出一只更乱蓬蓬那头乱草般的头发跟他有得一比的脑袋,在这乌黑的屋子里就象带了个伪装,眼力差点都看不出来。但李中吾早就在暗无天日的烂房子练就了夜猫般的好眼力,他甚至连“拐伯”还剩下多少只蛀牙都瞧得一清两楚。
这时他心中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的向那位叫“拐伯”的道,“你身上还有一个铜板吗。”果不其然,他从拐伯那里得到的,是一抹和他一样绝望的眼神,还有“咕噜”的一声回答。这回答其实并非来自于拐伯口中,而是来自于肚子中,李中吾甚至都搞不清楚这一声“饱噎”究竟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拐伯。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李中吾不算很穷呀,至少都还有下人使唤,拐伯是他的下人没错,但如果这个下人有地方去,应该也象其他他曾经拥有的999个下人般走个清光了。
连李中吾都不知道,这个叫拐伯的已经在他家呆多久了,可能连他爸爸都不知道,因为他爸爸未出生时,这拐伯就已经在他家当男佣了。反正至少都是他李家的三朝元老了。这老头也不知有多少年纪了,老得连牙齿都没有了,所以李中吾的眼力好不好不知道,但他不用瞧就知道拐伯有多少颗蛀牙倒是事实,因为不用瞧,他都清楚拐伯连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但李中吾却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自小就知道他因为左脚有点跛,所以大家都叫他拐伯,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因为在李中吾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有什么家人来探过他,相信也跟现在的李中吾一样,早就是个孤家寡人了。
这样一个又老又跛的人,除了跟着他这个自小他就服侍到大的“少爷”外,他还有什么地方好去,还能靠什么谋生呢?至少跟着李中吾虽然没什么好吃好住的,今天早上大少爷身上还有两个铜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能买了两个烧饼,各自分了一个吃。
至少大少爷都算对他不薄,甚至已真正达到有福有享,有难同当的高尚境界,这不,刚才他饿得肚子打咕噜时,大少爷都跟他一起担当了。
这世上到那里能找到这么好的主人哟,所以虽然少爷都半年不出柴门,但一日三餐(假如运气好的话还是有的,而不象今天早上到现在吃晚饭时候了才只吃了个烧饼)的工作,拐伯还是任劳任怨连用拐杖都感觉有点拐不起来却全部承担了下来。
能支撑他这样做下去的,除了少爷跟他同睡一间房同吃一块饼的一片良心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拐伯从小就没读过书,完全睁眼瞎一个。所以自小就很敬重有文化的人。少爷当然是个很有文化的人,自小就天资过人傲视同侪。拐伯还清楚的记得,少爷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时候全部拿了第一。记得当时老爷在少爷考了会试第一的时候,还在庄园里摆了九十九台筵席,当时真是来宾如云啊!唉,当时老爷的庄园多大啊,虽然摆了这么多台的酒席,却不过也只占老爷这庄园中的小小一角罢了。想到这里,拐伯不由在心里暗叹了一声。
他还记得,当时少爷的那些同学和他那位留着三绺老师,哦。。。,对了,叫什么孔老夫子的,还不停的向老爷恭贺,说什么贺喜少爷连中两元等等的。拐伯不知道这些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化人说的什么连中两元是什么意思,但他在旁边看到老爷笑得见牙不见齿的,自己也不由在一旁偷着乐。但让他更乐的是,那一天,拐伯吃到了他平生最好吃的一餐饭,虽然当然是剩饭,但都足够他回味很久了。什么海参鲍鱼,龙虾翅肚,这些在他那个穷乡下只是传说中的菜肴,后来他们收拾时可谓堆积如山。拐伯心想,老爷虽然富有却也是出身穷苦,平时一向都很节俭的,那天他如此罕见的铺张,可见少爷中了什么会。。。会元,他是多少的高兴哦。那几天我们这些下人吃得多开心啊!绝对是平生最丰盛的一次呀,拐伯记得,那一天的剩菜,他们这些下人几乎是开足了马力的狂吃,毕竟这么好的菜不是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后来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他们才心满意足的清理宴席,收拾碗筷。
“唉,那一天,简直是天堂上的日子啊!”拐伯现在已不由感叹出了声,他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他这种自小就捱饿的穷孩子,他只有个很朴素的想法,如果他能吃得饱就很满足了,如果能吃得好点,那简直就是天堂了。不但是拐伯,这也许是天朝很多朴实的很容易满足的农民的普遍想法吧。
拐伯不由又咂了咂嘴,忽然发觉自己那干瘪肚子似乎更饿了。他不由向少爷瞧了瞧,不知何时,少爷却又已拿起本不知什么书正看得津津有味,浑不象肚子饿了的样子,拐伯不觉一阵惭愧,自己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连少爷好象都未饿,怎么自己竟然会觉得饿了呢?
拐伯挺了挺肚子,假装自己刚饱餐了一顿鲍参翅肚了样子,脸上还浮起了一丝酒足饭饱般的微笑,又继续回忆起来。
唉,要不是老爷后来被奸人陷害,自己应该还会吃过很多次鲍参翅肚吧,这时拐伯忽然叹了口气,脸上居然起股恨意,在茅房顶空隙中透过的几缕光线的晃动下,他这股恨意让他那枯槁肌黄的脸看起来有几分狰狞。
也许这种神色,出现在一位行将就木,看惯风云的老人脸上是很不协调也很不正常的。但能让这个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视如无物的老人这么恨的,当然不会是后来他吃不到鲍参翅肚了,而是因为那个险恶的人和他那恶毒的人性。
拐伯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他的老爷、少爷,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恨那位所谓恶人。正所谓,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使卑微如拐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道理都是同样的。
拐伯头上忽然冒出了一阵冷汗,因为这时他的心忽然变得冷嗖嗖的,甚至比他那晚在知县门口接老爷回来时,那铺天盖地的宇宙历2002年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更冷。
那是少爷喜宴后的第二天,当天下了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但让李家上上下下心更冷的,却是发生在老爷身上的那件飞来横祸。
那天晚饭后,拐伯搭老爷去赴知县大人的一次邀约,他并不知他们之间谈些什么,只不过以为是一次平常的会晤。谁知他在外面这一等就是五个小时,当他再次见到老爷时,他就象条狗般被人扔了出来,全身上下血淋淋的,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地方。
拐伯用马车将老爷拉回去后,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最终只捱到第二天凌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去了,少爷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有多大,昨天才中了会元,今天就遭遇这样的变故,他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哦,这样的大喜大悲他怎么禁受得了。拐伯想到这里,感觉自己的眼睛变得有点湿湿的。
在老爷离世前的那天夜里,他们断断续续的了解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大概,原来那个知县王大人,一直觊觎老爷的财产,经常有意无意的暗示老爷要给他点好处,否则就要给老爷小鞋穿。可是老爷这人一贯刚直,又那会做那些行贿的事。总以为自己生意、做人都行得正站得直,而且他一贯看不起这位靠行贿、擦鞋而当了官的这位知县,平时都不屑与他为伍,又那会给这种人送什么礼呢?
老爷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平时我们这些下人自己或家里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很大方的周济的,但对于那种贪官,他不但不会赠予分毫,而且有一次还当着许多人的脸,将这位不要面皮,公然伸手要钱的贪官狠狠的斥责了一番。如此也就算了,老爷那次可能真的是太气愤了,他居然还将这位贪官为恶乡里,贪污受贿的事上报给了这位知县的上司,老爷为人一世英明,特别是在做生意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却怎么在这种事上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呢?现在的官那一个不是靠级级行贿上去的呢?知府要不是吃了这个知县的钱,怎么会将这个为害乡里,欺压勒索百姓的黑社会泼皮头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提为知县呢?而老爷现在却天真的到知府那里告这个知县行贿受贿,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老爷在各方面都出类拨萃,偏生在这方面却还心生侥幸,殊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道理,现在就是连三岁小儿都懂的。
老爷一生不勾结官府,能打拼出当时一片家业,普天之下都已算一个奇迹了。但现在到更大的贪官面前靠贪官,现在的官府已经腐败到如此田地,民又怎能与官斗,老爷又岂会有幸理?
拐伯越想越气,忽然右手狠狠一掌拍在自己大腿上,力道之大,令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又老又残又饿的老人之手。
果不其然,很快那位扶植王泼皮上位的知府大人就以老爷越级上访,不符诉讼程序为由,将老爷上告一案拨回给王泼皮审核。
这不是开玩笑吗这?这天底下还有如此腐败荒唐的官府吗?被告的人审核告状的人,这案件还用审吗?
这时拐伯的面上忽然现出一丝凄然的笑意,这丝笑意似乎让他那枯瘦的脸看上去没有那么狰狞了,却仿佛更让人害怕,因为这笑意中似乎包含着更多的仇恨。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了。
这件案件被转批回来的当晚,那知县小人果然阴险之极,他怕公然拘捕老爷会转移财产,为了达到全盘并吞的目的。竟假惺惺的派人向老爷邀约,道自己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诚心接受老爷的监督、批评,以后将积极退赃拒贿,为表感激悔改之意,特请老爷到其府上小酌几杯。。。
那时知道这消息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王知县一定是在扯谎,这人一贯品行恶劣,怎么一下就转了性了呢?岂不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吃肉的老虎怎么可能改吃素呢?但老爷却很信仰少爷的老师的孔老夫子那一套,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反过来批评大家太固执,把人性看得太卑劣了。
看来有文化是好的,但如果将书本的东西教条化了,不懂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完全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的话,就是孔夫子这个大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在现实中有时也不定对哦。拐伯似懂非懂的想着。
果真不幸被大家言中,老爷一进县衙,那个泼皮县长就露出了真面目。强迫老爷在他们拟好的莫须有罪状上签押。道老爷贩卖私盐,行贿官员,支持乱党,意图造反。。。罪大恶极,须将其财产充公。。。
这不是屈得就屈吗?老爷生意虽多,但八杆子都跟什么卖盐沾不上边呀。支持乱党,老爷这人一生谨小慎微,除了生意上的必要应酬,大门都不多出一步,何来什么乱党朋友呢?最离谱的还是什么行贿官员,老爷就是不愿也不想行贿才遭了这罪呀,现在却反倒成了他的罪名,这真是天大的讽刺阿!通篇也许就那句财产充公才是最靠谱的,他们罗列了这么多罪名,无非就是为了吞并老爷的财产而已。
可怜老爷当然不肯认罪,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还趁老爷昏迷时,硬将他手指按到罪状上按了指模,就这样当他认了罪。这世上还有公理吗?老爷一生光明磊落,老来却要受此等屈辱,一口气那能咽得下去,再加上又受到那些人的严刑拷打,两相折磨之下,终是捱不过第二天早上,就含恨而终了。
第二天一早,那个泼皮县长就派人来查封了老爷的财产,最惨的是老爷所有亲属子女,男的流放到边关服苦役,女的被分配到官家当奴婢。下面的佣人,也都跑得清光了。想不到含辛茹苦才打拼下的这番家业,居然最后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要不是这事情真的发生了,想必没人会相信这世上会发生如此荒唐透顶、灭绝人性的人间惨剧。
万幸的是,第二天少爷刚好回去还拜师恩,拜访亲友了,才险险逃过此却。当他晚上回来时,就如从天堂一下子掉进地狱般,已变成一个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了。
幸亏,当时还有拐伯,一个几百人口的,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的庄园,现在就只剩下的拐伯在他身旁。而也只有拐伯,才能让他这几十年来,不至于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原来他父亲当年,为了以后能落叶归根,却还在自己的老家建有一所大宅,而且里面还收藏有不少这些年来他购置下来价值连城的珍宝古玩,为了不走漏风声引来盗贼,这个大宅平时也就只有忠心耿耿,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拐伯有时回去打点看顾。其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妻妾儿女都无一人知晓。或许他想等到衣锦还乡的那一天才给他们一个惊喜吧,谁知他却终于没能等到那一天了。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他是没有看错的,那就是拐伯的人品,李中吾的父亲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也幸亏还有拐伯这样一个如此忠心如此重义的人,在那天后带他回到他父亲在老家建的宅第中,并靠着家里的那些珍玩古董,才让他过了这几十年虽然不耕不种不乞不讨,却至少能做到衣食无忧的日子。
这时拐伯脸上也浮上了层淡淡的笑意,不知是他想起自己这个卑微的人,终于对当年太老爷将他这个被人遗弃在路边,饿得奄奄一息的残疾儿的拾养救命之恩有了点回报。还是想起少爷平时跟他说起的那些宫闱情仇,诸侯争霸的有趣故事。
原来当年李中吾跟着拐伯逃离当地回到父亲的老家后,他一个舞象之年的少年,年纪轻轻就遭逢家庭如此变故,身心如何禁受得起。回来后不久就大病了一场,要不是有拐伯当时在一旁无微不至的照顾,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不过身病好医,心病却是再医不好了。自此后,他就心性大变,对什么官场仕途,竟已再提不起丁点兴趣。就连世间琐事,竟都觉得多余了。每天爱做的,也只是读书写书而已,父亲的惨遭横祸实在对他刺激太大,人性居然可以恶毒到如此程度,他要钻研出一本有关人性丑陋的作品,看看人的心能黑到什么程度。正因如此,现在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也就只有一个拐伯。
而拐伯,也的确值得他信任,因为这三十多年来,他除了读书写书,剩下的家务、杂工都让拐伯承包了,虽然他要求不太高,衣服可以三个月不换,吃饭有个烧饼也可,最多他就是闲暇时,或看书写书累了时,跟拐伯聊一下书里的趣事,或自己大作的精深,虽然也不知拐伯能不能听得懂,只是经常咧着个口嘿嘿地傻笑。但对于他这个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来说,这已经算是生活中一种难得的乐趣了。毕竟身边还有个这么忠实的听众。
但李中吾现在大作完成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闭关”也许时间真的有点太长了,不但拐伯早老得没牙了,原来自己也已一把年纪了。最惨的是父亲的那些家产都给他“挥霍一空”了,大作是完成了,但晚餐却没着落了。
李中吾现在已饿得看不下书了,他放下书本,心里颇是感慨了一番,他好象现在才意识到,他欠拐伯的实在太多了,拐伯如此无偿的照顾了他几十年,他现在居然连请拐伯吃个烧饼都请不起,这实在是让人于心难安呀,他不由有点歉疚的向拐伯坐的地方看去。却见拐伯坐的地方竟是空空如也,那有一个人在。
李中吾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已跟拐伯相处了几十年了,拐伯的性格他那有不知,除非有什么非离开不可的事,拐伯就当他是鸟巢中的小雏鸟,而拐伯就象只尽责的母鸟,是断不会贸然离开他的。而两人这几十年的相处下来,李中吾也已对拐伯有了种似乎比对父亲都更深厚的感情。
他匆忙起身,跑出家门四处呼喊张望,但四野茫茫,除了风雪呼号,那有拐伯的影子,在这样的风雪天气,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到野外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李中吾心里忽然涌起股不祥的预感,这感觉太可怕了,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他的额头居然沁出了一层汗水。
但现在想什么都是多余的,李中吾甚至已不敢再想,他只象只发狂的野狗般,四处呼号着搜寻着,直跑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他都没有找到拐伯,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了自己的那间草庐,期待着有奇迹发生,但终究,拐伯没有回来。
那一晚,李中吾没有整晚都没有睡,因为他哭了一晚,除了父亲死的那次,他还是第二次哭得那么伤心。
因为他知道,拐伯没有回来就是回不来了,否则他爬都会爬回来。他已经猜到拐伯为什么当时要离开他出去了,这让他哭得更伤心!
果然,第二天早上,当李中吾在昏昏沉沉中被人吵醒的时候,他开门时就见到了拐伯那僵硬的尸体,那是早起的邻居们在很远的地方发现的,跟他僵硬的身体一样僵硬的,是他瘦骨嶙峋的手上拿着的两个烧饼,还有他那脸上已被冻结了的僵硬的笑容。也许他临死时还在想,终于能给少爷找到晚餐了,终于可以庆祝一下少爷的大作完成了。所以,他去得很安祥,很欣慰。
看到这情景,连送他回来的邻里都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谁会想到,在这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卑微的老人身上,竟然会蕴含着这么伟大的人格呢!
但在他们伤感和愤怒的泪眼中,他们却居然只看到,李中吾只是冷漠的叫他们回去,甚至连感谢都不多一句。最后,这些热心的乡里,也只好咒骂着李中吾没良心,那样的天气还叫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去帮自己买东西,或者又叫嚷了几句他是个疯子诸如此类的话,怏怏然的散去了。
他们却不知道,李中吾的心在昨晚已经被自己的内疚冻得僵硬了,他的眼泪也已经流干了。现在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留待以后,当夜半梦回时,再象一只受伤的动物般,慢慢舔干自己伤口上的血而已。
但他现在必须做的,却是要将拐伯下葬,刚才在众人面前被误解奚落,他现在是断不能向别人开口借钱的了,何况以他的性格,就算没有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向人开口借钱都是件颇为踌躇的事。
环顾四周,自己剩下的,除了那本刚完成的《厚黑学》,满室唯有堆积如山的书籍矣。这些书籍花了他几十年时间才搜集得来,都是他心爱之物,如是平时,任是别人出再多价钱,他都是不肯随便转让的,但自己为之呕心呖血的作品刚完成,就遭遇如此变故,心里大感挫折,只觉自己奉为珍宝之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值钱。至少现在他最需要就不是书籍,而是能让拐伯能体面点下葬的一口棺椁
。
而要购买棺椁就需要钱,现在他能拿什么来换钱,举目看去,他这茅庐里除了书之外就那几件连收破旧佬可能都不要的破桌敝衣,李中吾不禁心里暗叹,想不到自己居然已沦落到如此田地,心里又是挣扎了一番,终于还是下定了主意。
接下来不久,他在屋边小溪胡乱喝了几口水充饥,修理了下实在太野人的胡子,找了件还算好点的衣服穿上,比较象个正常人之后,就背个破麻袋,装着自己认为不太合用的数十本书,到了附近的市集上,混杂在那些小摊小贩旁边,摆起了地摊。
可怜这么个几十年大门不出的人又如何会做生意呢?他用 一张烂席摆下了自己的那几十本书后,就垂着个头在那里算手指了。偶尔有几个无聊之人来看了看,他却将自己的头垂得更低了,就象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别人看他这样,本来想问下价的,但这世上那有这么怕羞的店主。所以当李中吾终于在摆摊半个小时后,鼓起最大的勇气抬起头的时候,他发觉他售卖的书已不见了一半。铜板却是一个都没。
还好有几个良心好点的,认为窃书不算偷,或者也象李中吾那般穷,或者良心有点发现,终究还是掉下了几个烂苹果呀咬过的馒头。当然,他们不知,现在这些东西对于李中吾来说,不异于珍馐美味,在其他小贩喊得天价响的叫卖声中,在旁人诧异的眼光中,李中吾终于填饱了肚子。但没有铜板,拐伯还是不能下葬的,没办法,李中吾还是要继续叫卖下去。
他还是垂着他的头,这时忽然旁边一阵惊呼,旁边的小贩象见了鬼一般在惊呼:“镇关西来了,走鬼!”然后是一阵鸡飞狗走,惊惶四散的噪音。李中吾大惊抬头,愕然发觉刚才还熙熙攘攘的市集突然间已变得冷冷清清,刚才他身边的那些小摊不知何时已走得一干两净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李中吾还未回过头来,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肚腩,他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一脸横肉,歪戴着一顶大檐帽的壮汉站在他面前,正用一双醉醺醺的眼睛斜睨着他,后面还跟着几个喽罗般的手下,个个杀气腾腾的样子。
李中吾这种几乎大辈子没出过门人那见过这种阵势,他本来就不擅言辞,现在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大盖帽似乎觉得他大不敬,突然气乎乎的一脚将的剩下的书连书带席都踢得四散飞去,口中嚷道,“你个死要饭的,见到我居然都不走,你是不是很嚣张?”
李中吾却不明白为什么见了他为什么要走,虽然这人的尊容未达到他见了就想亲上一口的地步,但也不至于一见就要走呀?他现在实在不知要如何回答,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只能很无辜的半张着口。
那盖帽大汉踢了他书,却见这人好象并不如何作怒,脸部又是如此一个表情,却也颇有点有气无处使之感。只能气哼哼的道,“我就是镇关西郑屠,渭州府城管大队大队长,这里的市场都归我管,你知道吗?在我的地头摆摊,没我的批准就是乱摆摊,明白吗?。。。”
他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中气十足,但李中吾却如何知道这些东东,他只懂天大地大,莫不是百姓土地,摆个小摊而已,居然都要被批准。他实在不懂这些,所以他只能继续沉默。
那个城管队长郑屠看他那副瘦骨啦叽衣衫褴褛的样子,看来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可能也觉无趣,这时高嚷了一声,“乱排摊,影响市容,将他的书没收充公,扯呼。”
李中吾只觉得他话音未落,这股人速度之快,几乎在他口都还未来得及合上的的当儿,这帮人已将他剩下的书收拾清光并走得没影了。
。。。。。。
李中吾都不知如何形容现在自己的感受,不过不论如何,他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做事的效率,这种效率绝对是久经磨练,工多手熟的结果。
从小他就明白,象他这种出身的,不比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自小家里人就已经给他们铺好了金光大道的富贵家庭子女。甚至比那些虽然贫穷但至少双亲健在、普通正常的家庭也是远比不上。因为他们的子女至少不会象他这样,自小就被人讥讽为“野种”
如果说出生于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对于秦烩来说,唯一还有点好处的话,那就是这种经历让他更早熟,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自己长大以后能出人头地,才能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并得到别人的敬畏。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读书科举一途了。所以,自小秦烩就比班上所有人读书都更努力,再加上他天生聪颖,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在17岁时就高中状元,自誉为“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当然后来有人考证,封川县文德乡(属现在封开县)出了个“岭南首魁状元”莫宣卿,高中时也只有17岁,却比秦烩迟出生了一天,他才应是“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因本文非是严肃学术论文,这里就不作甄别了。
且说秦烩高中状元后,以为这下终于时来运转,一抒抱负了。谁知皇帝除了在他状元及第那天在皇宫大殿上设宴并赐了他一杯酒后,就好象将他忘记得一干两净了一般。只让他任了个翰林院修撰的闲职,顾名思义,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干点啥的了吧?如果谁嫌自己的头发太浓密眼睛太明亮,那这份工作还算得上是不错的选择。具体点说,就是修正或考证“日暮苍山兰舟小 本无落霞缀清泉 去年叶落缘分定 死水微漾人却亡 ”之类的诗句究竟是李黑写的还是李白写的,并是否在这首诗中预言了日本去死,小泉定亡的谶语等无厘头的工作。
这还不算,这工作竟然一做还做了三十年,秦烩不但那一头浓密的热带雨林都熬成地中海了,
称呼上还多了个“三朝元老”的后缀,如果说这三十年时间里有了点成绩的话,就是在任职第28个年头的时候被现在的晕宗皇帝赐了个“内阁中书大学士”的虚衔,聊算个精神安慰吧。
“这王朝的皇帝都是些窝囊废,想不到自己堂堂一代状元,竟沦落到与鼠蚁为伴的下场,穷苦百姓培养一个人才容易吗?就这样给糟蹋了,何况自己。。。”仕途暗淡郁郁不得志,秦烩不免经常自怜自艾一番,特别是想到自己那倍加凄惨的童年时,几乎都不忍再想下去,但心中的怨气却又更添了几分。
这晚秦烩膳后正在厅里闲坐,这时忽有门僮来报,道有一旧友求见,秦烩不知是谁,挥手让门僮过去叫他进来,自已旋也整束衣冠,出去迎接。刚转过影壁,只见迎面而来的,赫然竟是小时学友,已有三十多年未见的―李中吾是也。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李中吾为何许人,其实说到他的著作,应该是市井文盲,都会略有所闻的了,不错,他就是著述有旷世奇书《厚黑学》的那个一代怪才李中吾是也。
李中吾小时跟秦烩少年同学,文采风流可谓一时瑜亮,不分轩轾。本来专心于功名的话,那一年的南京状元是他的而非秦烩的也说不定,但他偏生天生一副傲骨,为人清高自持。眼见官场腐败横行,官员贿赂成风,他一片仕途之心,不由早早的冷了下来。就在中了会元后不久,他就抛下了孔孟之书,归隐田园,醉心于研究社会百态,著书立说了。
秦烩跟他多年不见,关于他的状况也只是略有所闻。他在内心中虽对李中吾那种人生哲学不以为然,但毕竟同窗有年,且当年都是一代才子,心里不免有点惺惺相惜之心。何况两人多年不见,自己刚好今晚也满腹心事,有朋自远方来,煮酒论下英雄,不亦乐乎。于是两人略作寒暄,秦烩就命下人摆下酒席,两人下坐,不免一番觥筹交错。
几杯下肚,秦烩已有了几番酒意,今天能见旧友,心中自是高兴,但想想自己至今犹自潦倒,又是心生感触,不由长叹了口气。
李中吾正跟他喝得开心,正见他突然叹气,心下不解,讶然问道:“秦兄正喝得高兴,何故突然叹气呢?”
秦烩本是城府极深、内向寡言之人,平时心事都放心里,断不会随便跟别人提起的。但一来今天开心喝多了几杯;二来李中吾又非政界同僚,不虞酒后失言给传出去误事。最大的原因是,他现在的确是很想找个人倾诉下,难得碰到个如此适合的听众。于是在又长叹一声后,就将这些年来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股脑儿的向李中吾全倾诉了出来。
毕竟几十年的事了,即使秦烩已尽量说得简单扼要,还是花了差不多一支香的时间才好不容易说完。对秦烩来说,这可能是他平生以来,跟别人说过最多话的一次了。几乎是说得气喘吁吁、咳嗽连连,虽然说得辛苦,但将心里的苦水都倒了出来后,秦烩竟然感到心里有一种难得的舒畅感,心情好象也平和了许多。也难怪,象他这种平时做人总带着个面具,三闷棍都打不出一个响屁,除了尔虞我诈几乎没一个真心朋友的人,是很能会有这种畅尽所言的快感的。
这时秦烩拿眼光向李中吾瞧去,那眼神任谁都看得出,秦烩现在多希望从对方的口中听到些安慰及勉励的话,一个平时没什么朋友的人,也许有时内心里是特别的需要朋友的。
却见李中吾脸上似笑非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却口不作声,只是一味不停地向他劝酒,也不知他究竟有没有听清楚刚才秦烩在说什么,真是浪费了秦烩那好一番表情。
秦烩心下不乐,却又不好说什么,他本就是那种闷骚之人,这下又恢复了那种阴沉沉的的脸容,寻思。“自己真是自作多情,对牛弹琴了。”现在他只想这李中吾快点喝完酒,好结束这让他尴尬的场面。他却未想到原来自己连李中吾为何来到此地,为什么事来找他都未曾问过,只是大家一坐下就顾着向别人吐苦水。
原来这李中吾今天来找秦烩,内里却果真是有一番情由的。
且说当年李中吾归隐田园后,每日专注的,只是如何能写出本有关人性恶劣方面的专著,特别是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的发家史及统治史。人可能真是种奇怪的动物,象他这种无心于功名无心于政界发展的人,却偏偏在做学问方面对政治最感兴趣。于是在著书立说方面,也拣了这方面的主题来做。
这数十年来,他为了完成这方面的研究,那真可谓是穷经究典、呕心沥血矣。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三个月前,他那本花费了三十多年心血的巨著《厚黑学》终于问世了,这让他欣慰无比。但让他感到凄凉的是,为了写成这本书,他也将祖宗留下的,原本还算殷实的一份家产,挥霍了个一干两净。
也难怪,象他这种四肢不勤,大门不出,半年都不刮一次胡子,一年都不冲一次凉,身上那股咸鱼味连方圆五里的邻居都能闻到,除了看书就是写书的人。别人除了叫他“SB”,精神病之类,又还能叫他什么呢?更不幸的是,到李中吾大作完成时,他才仿佛发觉自己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原来祖宗留下的忒多珍玩古董。。。反正所有能给他拿来换钱的东西都早给他典当清光了。他现在除了一间茅庐和生活必需的一些台台凳凳,可说是,穷得只剩下书,因为不夸张点说,他那间烂房里几乎能塞得下的地方都塞满了书,他每次出入自己那间房子都可称得上是进行了一次体育运动。因为那书多得只能让他跳过去或侧着身慢慢地钻过去。
但李中吾现在才深切体会到,他小时候给私塾里那些教科书洗脑洗得有多厉害,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原来统统都不过是忽悠死人不包赔的歪理谬论。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那位人如其名身材高大的邓大平同志那句“实践是体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多么的正确。原来,挣钱才是硬道理,其他统统都是扯蛋。就象李中吾当时刚刚完成自己的巨著《厚黑学》时,当最初的喜极而泣过后,他发觉自己又要悲极而泣了。原来下一餐的饭钱没着落了。上天偏偏就这么捉弄人,连他想买个烧饼来庆贺数十年的心血结晶的钱竟然都没给他留下来。因为在他刚完成巨著后,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自己居然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有了。
李中吾悠悠地长叹了一口气,高呼了一声“拐伯”,很快就象变戏法一般,他那乱蓬蓬的书堆中忽然伸出一只更乱蓬蓬那头乱草般的头发跟他有得一比的脑袋,在这乌黑的屋子里就象带了个伪装,眼力差点都看不出来。但李中吾早就在暗无天日的烂房子练就了夜猫般的好眼力,他甚至连“拐伯”还剩下多少只蛀牙都瞧得一清两楚。
这时他心中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的向那位叫“拐伯”的道,“你身上还有一个铜板吗。”果不其然,他从拐伯那里得到的,是一抹和他一样绝望的眼神,还有“咕噜”的一声回答。这回答其实并非来自于拐伯口中,而是来自于肚子中,李中吾甚至都搞不清楚这一声“饱噎”究竟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拐伯。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李中吾不算很穷呀,至少都还有下人使唤,拐伯是他的下人没错,但如果这个下人有地方去,应该也象其他他曾经拥有的999个下人般走个清光了。
连李中吾都不知道,这个叫拐伯的已经在他家呆多久了,可能连他爸爸都不知道,因为他爸爸未出生时,这拐伯就已经在他家当男佣了。反正至少都是他李家的三朝元老了。这老头也不知有多少年纪了,老得连牙齿都没有了,所以李中吾的眼力好不好不知道,但他不用瞧就知道拐伯有多少颗蛀牙倒是事实,因为不用瞧,他都清楚拐伯连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但李中吾却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自小就知道他因为左脚有点跛,所以大家都叫他拐伯,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因为在李中吾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有什么家人来探过他,相信也跟现在的李中吾一样,早就是个孤家寡人了。
这样一个又老又跛的人,除了跟着他这个自小他就服侍到大的“少爷”外,他还有什么地方好去,还能靠什么谋生呢?至少跟着李中吾虽然没什么好吃好住的,今天早上大少爷身上还有两个铜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能买了两个烧饼,各自分了一个吃。
至少大少爷都算对他不薄,甚至已真正达到有福有享,有难同当的高尚境界,这不,刚才他饿得肚子打咕噜时,大少爷都跟他一起担当了。
这世上到那里能找到这么好的主人哟,所以虽然少爷都半年不出柴门,但一日三餐(假如运气好的话还是有的,而不象今天早上到现在吃晚饭时候了才只吃了个烧饼)的工作,拐伯还是任劳任怨连用拐杖都感觉有点拐不起来却全部承担了下来。
能支撑他这样做下去的,除了少爷跟他同睡一间房同吃一块饼的一片良心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拐伯从小就没读过书,完全睁眼瞎一个。所以自小就很敬重有文化的人。少爷当然是个很有文化的人,自小就天资过人傲视同侪。拐伯还清楚的记得,少爷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时候全部拿了第一。记得当时老爷在少爷考了会试第一的时候,还在庄园里摆了九十九台筵席,当时真是来宾如云啊!唉,当时老爷的庄园多大啊,虽然摆了这么多台的酒席,却不过也只占老爷这庄园中的小小一角罢了。想到这里,拐伯不由在心里暗叹了一声。
他还记得,当时少爷的那些同学和他那位留着三绺老师,哦。。。,对了,叫什么孔老夫子的,还不停的向老爷恭贺,说什么贺喜少爷连中两元等等的。拐伯不知道这些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化人说的什么连中两元是什么意思,但他在旁边看到老爷笑得见牙不见齿的,自己也不由在一旁偷着乐。但让他更乐的是,那一天,拐伯吃到了他平生最好吃的一餐饭,虽然当然是剩饭,但都足够他回味很久了。什么海参鲍鱼,龙虾翅肚,这些在他那个穷乡下只是传说中的菜肴,后来他们收拾时可谓堆积如山。拐伯心想,老爷虽然富有却也是出身穷苦,平时一向都很节俭的,那天他如此罕见的铺张,可见少爷中了什么会。。。会元,他是多少的高兴哦。那几天我们这些下人吃得多开心啊!绝对是平生最丰盛的一次呀,拐伯记得,那一天的剩菜,他们这些下人几乎是开足了马力的狂吃,毕竟这么好的菜不是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后来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他们才心满意足的清理宴席,收拾碗筷。
“唉,那一天,简直是天堂上的日子啊!”拐伯现在已不由感叹出了声,他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他这种自小就捱饿的穷孩子,他只有个很朴素的想法,如果他能吃得饱就很满足了,如果能吃得好点,那简直就是天堂了。不但是拐伯,这也许是天朝很多朴实的很容易满足的农民的普遍想法吧。
拐伯不由又咂了咂嘴,忽然发觉自己那干瘪肚子似乎更饿了。他不由向少爷瞧了瞧,不知何时,少爷却又已拿起本不知什么书正看得津津有味,浑不象肚子饿了的样子,拐伯不觉一阵惭愧,自己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连少爷好象都未饿,怎么自己竟然会觉得饿了呢?
拐伯挺了挺肚子,假装自己刚饱餐了一顿鲍参翅肚了样子,脸上还浮起了一丝酒足饭饱般的微笑,又继续回忆起来。
唉,要不是老爷后来被奸人陷害,自己应该还会吃过很多次鲍参翅肚吧,这时拐伯忽然叹了口气,脸上居然起股恨意,在茅房顶空隙中透过的几缕光线的晃动下,他这股恨意让他那枯槁肌黄的脸看起来有几分狰狞。
也许这种神色,出现在一位行将就木,看惯风云的老人脸上是很不协调也很不正常的。但能让这个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视如无物的老人这么恨的,当然不会是后来他吃不到鲍参翅肚了,而是因为那个险恶的人和他那恶毒的人性。
拐伯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他的老爷、少爷,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恨那位所谓恶人。正所谓,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使卑微如拐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道理都是同样的。
拐伯头上忽然冒出了一阵冷汗,因为这时他的心忽然变得冷嗖嗖的,甚至比他那晚在知县门口接老爷回来时,那铺天盖地的宇宙历2002年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更冷。
那是少爷喜宴后的第二天,当天下了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但让李家上上下下心更冷的,却是发生在老爷身上的那件飞来横祸。
那天晚饭后,拐伯搭老爷去赴知县大人的一次邀约,他并不知他们之间谈些什么,只不过以为是一次平常的会晤。谁知他在外面这一等就是五个小时,当他再次见到老爷时,他就象条狗般被人扔了出来,全身上下血淋淋的,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地方。
拐伯用马车将老爷拉回去后,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最终只捱到第二天凌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去了,少爷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有多大,昨天才中了会元,今天就遭遇这样的变故,他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哦,这样的大喜大悲他怎么禁受得了。拐伯想到这里,感觉自己的眼睛变得有点湿湿的。
在老爷离世前的那天夜里,他们断断续续的了解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大概,原来那个知县王大人,一直觊觎老爷的财产,经常有意无意的暗示老爷要给他点好处,否则就要给老爷小鞋穿。可是老爷这人一贯刚直,又那会做那些行贿的事。总以为自己生意、做人都行得正站得直,而且他一贯看不起这位靠行贿、擦鞋而当了官的这位知县,平时都不屑与他为伍,又那会给这种人送什么礼呢?
老爷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平时我们这些下人自己或家里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很大方的周济的,但对于那种贪官,他不但不会赠予分毫,而且有一次还当着许多人的脸,将这位不要面皮,公然伸手要钱的贪官狠狠的斥责了一番。如此也就算了,老爷那次可能真的是太气愤了,他居然还将这位贪官为恶乡里,贪污受贿的事上报给了这位知县的上司,老爷为人一世英明,特别是在做生意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却怎么在这种事上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呢?现在的官那一个不是靠级级行贿上去的呢?知府要不是吃了这个知县的钱,怎么会将这个为害乡里,欺压勒索百姓的黑社会泼皮头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提为知县呢?而老爷现在却天真的到知府那里告这个知县行贿受贿,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老爷在各方面都出类拨萃,偏生在这方面却还心生侥幸,殊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道理,现在就是连三岁小儿都懂的。
老爷一生不勾结官府,能打拼出当时一片家业,普天之下都已算一个奇迹了。但现在到更大的贪官面前靠贪官,现在的官府已经腐败到如此田地,民又怎能与官斗,老爷又岂会有幸理?
拐伯越想越气,忽然右手狠狠一掌拍在自己大腿上,力道之大,令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又老又残又饿的老人之手。
果不其然,很快那位扶植王泼皮上位的知府大人就以老爷越级上访,不符诉讼程序为由,将老爷上告一案拨回给王泼皮审核。
这不是开玩笑吗这?这天底下还有如此腐败荒唐的官府吗?被告的人审核告状的人,这案件还用审吗?
这时拐伯的面上忽然现出一丝凄然的笑意,这丝笑意似乎让他那枯瘦的脸看上去没有那么狰狞了,却仿佛更让人害怕,因为这笑意中似乎包含着更多的仇恨。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了。
这件案件被转批回来的当晚,那知县小人果然阴险之极,他怕公然拘捕老爷会转移财产,为了达到全盘并吞的目的。竟假惺惺的派人向老爷邀约,道自己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诚心接受老爷的监督、批评,以后将积极退赃拒贿,为表感激悔改之意,特请老爷到其府上小酌几杯。。。
那时知道这消息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王知县一定是在扯谎,这人一贯品行恶劣,怎么一下就转了性了呢?岂不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吃肉的老虎怎么可能改吃素呢?但老爷却很信仰少爷的老师的孔老夫子那一套,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反过来批评大家太固执,把人性看得太卑劣了。
看来有文化是好的,但如果将书本的东西教条化了,不懂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完全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的话,就是孔夫子这个大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在现实中有时也不定对哦。拐伯似懂非懂的想着。
果真不幸被大家言中,老爷一进县衙,那个泼皮县长就露出了真面目。强迫老爷在他们拟好的莫须有罪状上签押。道老爷贩卖私盐,行贿官员,支持乱党,意图造反。。。罪大恶极,须将其财产充公。。。
这不是屈得就屈吗?老爷生意虽多,但八杆子都跟什么卖盐沾不上边呀。支持乱党,老爷这人一生谨小慎微,除了生意上的必要应酬,大门都不多出一步,何来什么乱党朋友呢?最离谱的还是什么行贿官员,老爷就是不愿也不想行贿才遭了这罪呀,现在却反倒成了他的罪名,这真是天大的讽刺阿!通篇也许就那句财产充公才是最靠谱的,他们罗列了这么多罪名,无非就是为了吞并老爷的财产而已。
可怜老爷当然不肯认罪,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还趁老爷昏迷时,硬将他手指按到罪状上按了指模,就这样当他认了罪。这世上还有公理吗?老爷一生光明磊落,老来却要受此等屈辱,一口气那能咽得下去,再加上又受到那些人的严刑拷打,两相折磨之下,终是捱不过第二天早上,就含恨而终了。
第二天一早,那个泼皮县长就派人来查封了老爷的财产,最惨的是老爷所有亲属子女,男的流放到边关服苦役,女的被分配到官家当奴婢。下面的佣人,也都跑得清光了。想不到含辛茹苦才打拼下的这番家业,居然最后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要不是这事情真的发生了,想必没人会相信这世上会发生如此荒唐透顶、灭绝人性的人间惨剧。
万幸的是,第二天少爷刚好回去还拜师恩,拜访亲友了,才险险逃过此却。当他晚上回来时,就如从天堂一下子掉进地狱般,已变成一个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了。
幸亏,当时还有拐伯,一个几百人口的,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的庄园,现在就只剩下的拐伯在他身旁。而也只有拐伯,才能让他这几十年来,不至于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原来他父亲当年,为了以后能落叶归根,却还在自己的老家建有一所大宅,而且里面还收藏有不少这些年来他购置下来价值连城的珍宝古玩,为了不走漏风声引来盗贼,这个大宅平时也就只有忠心耿耿,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拐伯有时回去打点看顾。其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妻妾儿女都无一人知晓。或许他想等到衣锦还乡的那一天才给他们一个惊喜吧,谁知他却终于没能等到那一天了。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他是没有看错的,那就是拐伯的人品,李中吾的父亲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也幸亏还有拐伯这样一个如此忠心如此重义的人,在那天后带他回到他父亲在老家建的宅第中,并靠着家里的那些珍玩古董,才让他过了这几十年虽然不耕不种不乞不讨,却至少能做到衣食无忧的日子。
这时拐伯脸上也浮上了层淡淡的笑意,不知是他想起自己这个卑微的人,终于对当年太老爷将他这个被人遗弃在路边,饿得奄奄一息的残疾儿的拾养救命之恩有了点回报。还是想起少爷平时跟他说起的那些宫闱情仇,诸侯争霸的有趣故事。
原来当年李中吾跟着拐伯逃离当地回到父亲的老家后,他一个舞象之年的少年,年纪轻轻就遭逢家庭如此变故,身心如何禁受得起。回来后不久就大病了一场,要不是有拐伯当时在一旁无微不至的照顾,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不过身病好医,心病却是再医不好了。自此后,他就心性大变,对什么官场仕途,竟已再提不起丁点兴趣。就连世间琐事,竟都觉得多余了。每天爱做的,也只是读书写书而已,父亲的惨遭横祸实在对他刺激太大,人性居然可以恶毒到如此程度,他要钻研出一本有关人性丑陋的作品,看看人的心能黑到什么程度。正因如此,现在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也就只有一个拐伯。
而拐伯,也的确值得他信任,因为这三十多年来,他除了读书写书,剩下的家务、杂工都让拐伯承包了,虽然他要求不太高,衣服可以三个月不换,吃饭有个烧饼也可,最多他就是闲暇时,或看书写书累了时,跟拐伯聊一下书里的趣事,或自己大作的精深,虽然也不知拐伯能不能听得懂,只是经常咧着个口嘿嘿地傻笑。但对于他这个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来说,这已经算是生活中一种难得的乐趣了。毕竟身边还有个这么忠实的听众。
但李中吾现在大作完成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闭关”也许时间真的有点太长了,不但拐伯早老得没牙了,原来自己也已一把年纪了。最惨的是父亲的那些家产都给他“挥霍一空”了,大作是完成了,但晚餐却没着落了。
李中吾现在已饿得看不下书了,他放下书本,心里颇是感慨了一番,他好象现在才意识到,他欠拐伯的实在太多了,拐伯如此无偿的照顾了他几十年,他现在居然连请拐伯吃个烧饼都请不起,这实在是让人于心难安呀,他不由有点歉疚的向拐伯坐的地方看去。却见拐伯坐的地方竟是空空如也,那有一个人在。
李中吾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已跟拐伯相处了几十年了,拐伯的性格他那有不知,除非有什么非离开不可的事,拐伯就当他是鸟巢中的小雏鸟,而拐伯就象只尽责的母鸟,是断不会贸然离开他的。而两人这几十年的相处下来,李中吾也已对拐伯有了种似乎比对父亲都更深厚的感情。
他匆忙起身,跑出家门四处呼喊张望,但四野茫茫,除了风雪呼号,那有拐伯的影子,在这样的风雪天气,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到野外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李中吾心里忽然涌起股不祥的预感,这感觉太可怕了,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他的额头居然沁出了一层汗水。
但现在想什么都是多余的,李中吾甚至已不敢再想,他只象只发狂的野狗般,四处呼号着搜寻着,直跑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他都没有找到拐伯,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了自己的那间草庐,期待着有奇迹发生,但终究,拐伯没有回来。
那一晚,李中吾没有整晚都没有睡,因为他哭了一晚,除了父亲死的那次,他还是第二次哭得那么伤心。
因为他知道,拐伯没有回来就是回不来了,否则他爬都会爬回来。他已经猜到拐伯为什么当时要离开他出去了,这让他哭得更伤心!
果然,第二天早上,当李中吾在昏昏沉沉中被人吵醒的时候,他开门时就见到了拐伯那僵硬的尸体,那是早起的邻居们在很远的地方发现的,跟他僵硬的身体一样僵硬的,是他瘦骨嶙峋的手上拿着的两个烧饼,还有他那脸上已被冻结了的僵硬的笑容。也许他临死时还在想,终于能给少爷找到晚餐了,终于可以庆祝一下少爷的大作完成了。所以,他去得很安祥,很欣慰。
看到这情景,连送他回来的邻里都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谁会想到,在这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卑微的老人身上,竟然会蕴含着这么伟大的人格呢!
但在他们伤感和愤怒的泪眼中,他们却居然只看到,李中吾只是冷漠的叫他们回去,甚至连感谢都不多一句。最后,这些热心的乡里,也只好咒骂着李中吾没良心,那样的天气还叫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去帮自己买东西,或者又叫嚷了几句他是个疯子诸如此类的话,怏怏然的散去了。
他们却不知道,李中吾的心在昨晚已经被自己的内疚冻得僵硬了,他的眼泪也已经流干了。现在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留待以后,当夜半梦回时,再象一只受伤的动物般,慢慢舔干自己伤口上的血而已。
但他现在必须做的,却是要将拐伯下葬,刚才在众人面前被误解奚落,他现在是断不能向别人开口借钱的了,何况以他的性格,就算没有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向人开口借钱都是件颇为踌躇的事。
环顾四周,自己剩下的,除了那本刚完成的《厚黑学》,满室唯有堆积如山的书籍矣。这些书籍花了他几十年时间才搜集得来,都是他心爱之物,如是平时,任是别人出再多价钱,他都是不肯随便转让的,但自己为之呕心呖血的作品刚完成,就遭遇如此变故,心里大感挫折,只觉自己奉为珍宝之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值钱。至少现在他最需要就不是书籍,而是能让拐伯能体面点下葬的一口棺椁
。
而要购买棺椁就需要钱,现在他能拿什么来换钱,举目看去,他这茅庐里除了书之外就那几件连收破旧佬可能都不要的破桌敝衣,李中吾不禁心里暗叹,想不到自己居然已沦落到如此田地,心里又是挣扎了一番,终于还是下定了主意。
接下来不久,他在屋边小溪胡乱喝了几口水充饥,修理了下实在太野人的胡子,找了件还算好点的衣服穿上,比较象个正常人之后,就背个破麻袋,装着自己认为不太合用的数十本书,到了附近的市集上,混杂在那些小摊小贩旁边,摆起了地摊。
可怜这么个几十年大门不出的人又如何会做生意呢?他用 一张烂席摆下了自己的那几十本书后,就垂着个头在那里算手指了。偶尔有几个无聊之人来看了看,他却将自己的头垂得更低了,就象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别人看他这样,本来想问下价的,但这世上那有这么怕羞的店主。所以当李中吾终于在摆摊半个小时后,鼓起最大的勇气抬起头的时候,他发觉他售卖的书已不见了一半。铜板却是一个都没。
还好有几个良心好点的,认为窃书不算偷,或者也象李中吾那般穷,或者良心有点发现,终究还是掉下了几个烂苹果呀咬过的馒头。当然,他们不知,现在这些东西对于李中吾来说,不异于珍馐美味,在其他小贩喊得天价响的叫卖声中,在旁人诧异的眼光中,李中吾终于填饱了肚子。但没有铜板,拐伯还是不能下葬的,没办法,李中吾还是要继续叫卖下去。
他还是垂着他的头,这时忽然旁边一阵惊呼,旁边的小贩象见了鬼一般在惊呼:“镇关西来了,走鬼!”然后是一阵鸡飞狗走,惊惶四散的噪音。李中吾大惊抬头,愕然发觉刚才还熙熙攘攘的市集突然间已变得冷冷清清,刚才他身边的那些小摊不知何时已走得一干两净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李中吾还未回过头来,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肚腩,他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一脸横肉,歪戴着一顶大檐帽的壮汉站在他面前,正用一双醉醺醺的眼睛斜睨着他,后面还跟着几个喽罗般的手下,个个杀气腾腾的样子。
李中吾这种几乎大辈子没出过门人那见过这种阵势,他本来就不擅言辞,现在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大盖帽似乎觉得他大不敬,突然气乎乎的一脚将的剩下的书连书带席都踢得四散飞去,口中嚷道,“你个死要饭的,见到我居然都不走,你是不是很嚣张?”
李中吾却不明白为什么见了他为什么要走,虽然这人的尊容未达到他见了就想亲上一口的地步,但也不至于一见就要走呀?他现在实在不知要如何回答,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只能很无辜的半张着口。
那盖帽大汉踢了他书,却见这人好象并不如何作怒,脸部又是如此一个表情,却也颇有点有气无处使之感。只能气哼哼的道,“我就是镇关西郑屠,渭州府城管大队大队长,这里的市场都归我管,你知道吗?在我的地头摆摊,没我的批准就是乱摆摊,明白吗?。。。”
他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中气十足,但李中吾却如何知道这些东东,他只懂天大地大,莫不是百姓土地,摆个小摊而已,居然都要被批准。他实在不懂这些,所以他只能继续沉默。
那个城管队长郑屠看他那副瘦骨啦叽衣衫褴褛的样子,看来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可能也觉无趣,这时高嚷了一声,“乱排摊,影响市容,将他的书没收充公,扯呼。”
李中吾只觉得他话音未落,这股人速度之快,几乎在他口都还未来得及合上的的当儿,这帮人已将他剩下的书收拾清光并走得没影了。
。。。。。。
李中吾都不知如何形容现在自己的感受,不过不论如何,他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做事的效率,这种效率绝对是久经磨练,工多手熟的结果。
- 注册
- 2007-04-22
- 帖子
- 5,300
- 反馈评分
- 2
- 点数
- 0
QUOTE(蛙子 @ 2009年10月24日 Saturday, 08:20 PM)
少年多梦,人皆如此,即使有些梦是很荒唐和很好笑的,也属正常。秦烩少时虽也象许多同龄人般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梦。但他出身寒微且命运多舛,却难得的较之一般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和现实。
从小他就明白,象他这种出身的,不比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自小家里人就已经给他们铺好了金光大道的富贵家庭子女。甚至比那些虽然贫穷但至少双亲健在、普通正常的家庭也是远比不上。因为他们的子女至少不会象他这样,自小就被人讥讽为“野种”
如果说出生于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对于秦烩来说,唯一还有点好处的话,那就是这种经历让他更早熟,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自己长大以后能出人头地,才能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并得到别人的敬畏。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读书科举一途了。所以,自小秦烩就比班上所有人读书都更努力,再加上他天生聪颖,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在17岁时就高中状元,自誉为“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当然后来有人考证,封川县文德乡(属现在封开县)出了个“岭南首魁状元”莫宣卿,高中时也只有17岁,却比秦烩迟出生了一天,他才应是“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因本文非是严肃学术论文,这里就不作甄别了。
且说秦烩高中状元后,以为这下终于时来运转,一抒抱负了。谁知皇帝除了在他状元及第那天在皇宫大殿上设宴并赐了他一杯酒后,就好象将他忘记得一干两净了一般。只让他任了个翰林院修撰的闲职,顾名思义,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干点啥的了吧?如果谁嫌自己的头发太浓密眼睛太明亮,那这份工作还算得上是不错的选择。具体点说,就是修正或考证“日暮苍山兰舟小 本无落霞缀清泉 去年叶落缘分定 死水微漾人却亡 ”之类的诗句究竟是李黑写的还是李白写的,并是否在这首诗中预言了日本去死,小泉定亡的谶语等无厘头的工作。
这还不算,这工作竟然一做还做了三十年,秦烩不但那一头浓密的热带雨林都熬成地中海了,
称呼上还多了个“三朝元老”的后缀,如果说这三十年时间里有了点成绩的话,就是在任职第28个年头的时候被现在的晕宗皇帝赐了个“内阁中书大学士”的虚衔,聊算个精神安慰吧。
“这王朝的皇帝都是些窝囊废,想不到自己堂堂一代状元,竟沦落到与鼠蚁为伴的下场,穷苦百姓培养一个人才容易吗?就这样给糟蹋了,何况自己。。。”仕途暗淡郁郁不得志,秦烩不免经常自怜自艾一番,特别是想到自己那倍加凄惨的童年时,几乎都不忍再想下去,但心中的怨气却又更添了几分。
这晚秦烩膳后正在厅里闲坐,这时忽有门僮来报,道有一旧友求见,秦烩不知是谁,挥手让门僮过去叫他进来,自已旋也整束衣冠,出去迎接。刚转过影壁,只见迎面而来的,赫然竟是小时学友,已有三十多年未见的―李中吾是也。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李中吾为何许人,其实说到他的著作,应该是市井文盲,都会略有所闻的了,不错,他就是著述有旷世奇书《厚黑学》的那个一代怪才李中吾是也。
李中吾小时跟秦烩少年同学,文采风流可谓一时瑜亮,不分轩轾。本来专心于功名的话,那一年的南京状元是他的而非秦烩的也说不定,但他偏生天生一副傲骨,为人清高自持。眼见官场腐败横行,官员贿赂成风,他一片仕途之心,不由早早的冷了下来。就在中了会元后不久,他就抛下了孔孟之书,归隐田园,醉心于研究社会百态,著书立说了。
秦烩跟他多年不见,关于他的状况也只是略有所闻。他在内心中虽对李中吾那种人生哲学不以为然,但毕竟同窗有年,且当年都是一代才子,心里不免有点惺惺相惜之心。何况两人多年不见,自己刚好今晚也满腹心事,有朋自远方来,煮酒论下英雄,不亦乐乎。于是两人略作寒暄,秦烩就命下人摆下酒席,两人下坐,不免一番觥筹交错。
几杯下肚,秦烩已有了几番酒意,今天能见旧友,心中自是高兴,但想想自己至今犹自潦倒,又是心生感触,不由长叹了口气。
李中吾正跟他喝得开心,正见他突然叹气,心下不解,讶然问道:“秦兄正喝得高兴,何故突然叹气呢?”
秦烩本是城府极深、内向寡言之人,平时心事都放心里,断不会随便跟别人提起的。但一来今天开心喝多了几杯;二来李中吾又非政界同僚,不虞酒后失言给传出去误事。最大的原因是,他现在的确是很想找个人倾诉下,难得碰到个如此适合的听众。于是在又长叹一声后,就将这些年来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股脑儿的向李中吾全倾诉了出来。
毕竟几十年的事了,即使秦烩已尽量说得简单扼要,还是花了差不多一支香的时间才好不容易说完。对秦烩来说,这可能是他平生以来,跟别人说过最多话的一次了。几乎是说得气喘吁吁、咳嗽连连,虽然说得辛苦,但将心里的苦水都倒了出来后,秦烩竟然感到心里有一种难得的舒畅感,心情好象也平和了许多。也难怪,象他这种平时做人总带着个面具,三闷棍都打不出一个响屁,除了尔虞我诈几乎没一个真心朋友的人,是很能会有这种畅尽所言的快感的。
这时秦烩拿眼光向李中吾瞧去,那眼神任谁都看得出,秦烩现在多希望从对方的口中听到些安慰及勉励的话,一个平时没什么朋友的人,也许有时内心里是特别的需要朋友的。
却见李中吾脸上似笑非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却口不作声,只是一味不停地向他劝酒,也不知他究竟有没有听清楚刚才秦烩在说什么,真是浪费了秦烩那好一番表情。
秦烩心下不乐,却又不好说什么,他本就是那种闷骚之人,这下又恢复了那种阴沉沉的的脸容,寻思。“自己真是自作多情,对牛弹琴了。”现在他只想这李中吾快点喝完酒,好结束这让他尴尬的场面。他却未想到原来自己连李中吾为何来到此地,为什么事来找他都未曾问过,只是大家一坐下就顾着向别人吐苦水。
原来这李中吾今天来找秦烩,内里却果真是有一番情由的。
且说当年李中吾归隐田园后,每日专注的,只是如何能写出本有关人性恶劣方面的专著,特别是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的发家史及统治史。人可能真是种奇怪的动物,象他这种无心于功名无心于政界发展的人,却偏偏在做学问方面对政治最感兴趣。于是在著书立说方面,也拣了这方面的主题来做。
这数十年来,他为了完成这方面的研究,那真可谓是穷经究典、呕心沥血矣。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三个月前,他那本花费了三十多年心血的巨著《厚黑学》终于问世了,这让他欣慰无比。但让他感到凄凉的是,为了写成这本书,他也将祖宗留下的,原本还算殷实的一份家产,挥霍了个一干两净。
也难怪,象他这种四肢不勤,大门不出,半年都不刮一次胡子,一年都不冲一次凉,身上那股咸鱼味连方圆五里的邻居都能闻到,除了看书就是写书的人。别人除了叫他“SB”,精神病之类,又还能叫他什么呢?更不幸的是,到李中吾大作完成时,他才仿佛发觉自己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原来祖宗留下的忒多珍玩古董。。。反正所有能给他拿来换钱的东西都早给他典当清光了。他现在除了一间茅庐和生活必需的一些台台凳凳,可说是,穷得只剩下书,因为不夸张点说,他那间烂房里几乎能塞得下的地方都塞满了书,他每次出入自己那间房子都可称得上是进行了一次体育运动。因为那书多得只能让他跳过去或侧着身慢慢地钻过去。
但李中吾现在才深切体会到,他小时候给私塾里那些教科书洗脑洗得有多厉害,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原来统统都不过是忽悠死人不包赔的歪理谬论。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那位人如其名身材高大的邓大平同志那句“实践是体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多么的正确。原来,挣钱才是硬道理,其他统统都是扯蛋。就象李中吾当时刚刚完成自己的巨著《厚黑学》时,当最初的喜极而泣过后,他发觉自己又要悲极而泣了。原来下一餐的饭钱没着落了。上天偏偏就这么捉弄人,连他想买个烧饼来庆贺数十年的心血结晶的钱竟然都没给他留下来。因为在他刚完成巨著后,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自己居然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有了。
李中吾悠悠地长叹了一口气,高呼了一声“拐伯”,很快就象变戏法一般,他那乱蓬蓬的书堆中忽然伸出一只更乱蓬蓬那头乱草般的头发跟他有得一比的脑袋,在这乌黑的屋子里就象带了个伪装,眼力差点都看不出来。但李中吾早就在暗无天日的烂房子练就了夜猫般的好眼力,他甚至连“拐伯”还剩下多少只蛀牙都瞧得一清两楚。
这时他心中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的向那位叫“拐伯”的道,“你身上还有一个铜板吗。”果不其然,他从拐伯那里得到的,是一抹和他一样绝望的眼神,还有“咕噜”的一声回答。这回答其实并非来自于拐伯口中,而是来自于肚子中,李中吾甚至都搞不清楚这一声“饱噎”究竟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拐伯。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李中吾不算很穷呀,至少都还有下人使唤,拐伯是他的下人没错,但如果这个下人有地方去,应该也象其他他曾经拥有的999个下人般走个清光了。
连李中吾都不知道,这个叫拐伯的已经在他家呆多久了,可能连他爸爸都不知道,因为他爸爸未出生时,这拐伯就已经在他家当男佣了。反正至少都是他李家的三朝元老了。这老头也不知有多少年纪了,老得连牙齿都没有了,所以李中吾的眼力好不好不知道,但他不用瞧就知道拐伯有多少颗蛀牙倒是事实,因为不用瞧,他都清楚拐伯连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但李中吾却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自小就知道他因为左脚有点跛,所以大家都叫他拐伯,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因为在李中吾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有什么家人来探过他,相信也跟现在的李中吾一样,早就是个孤家寡人了。
这样一个又老又跛的人,除了跟着他这个自小他就服侍到大的“少爷”外,他还有什么地方好去,还能靠什么谋生呢?至少跟着李中吾虽然没什么好吃好住的,今天早上大少爷身上还有两个铜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能买了两个烧饼,各自分了一个吃。
至少大少爷都算对他不薄,甚至已真正达到有福有享,有难同当的高尚境界,这不,刚才他饿得肚子打咕噜时,大少爷都跟他一起担当了。
这世上到那里能找到这么好的主人哟,所以虽然少爷都半年不出柴门,但一日三餐(假如运气好的话还是有的,而不象今天早上到现在吃晚饭时候了才只吃了个烧饼)的工作,拐伯还是任劳任怨连用拐杖都感觉有点拐不起来却全部承担了下来。
能支撑他这样做下去的,除了少爷跟他同睡一间房同吃一块饼的一片良心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拐伯从小就没读过书,完全睁眼瞎一个。所以自小就很敬重有文化的人。少爷当然是个很有文化的人,自小就天资过人傲视同侪。拐伯还清楚的记得,少爷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时候全部拿了第一。记得当时老爷在少爷考了会试第一的时候,还在庄园里摆了九十九台筵席,当时真是来宾如云啊!唉,当时老爷的庄园多大啊,虽然摆了这么多台的酒席,却不过也只占老爷这庄园中的小小一角罢了。想到这里,拐伯不由在心里暗叹了一声。
他还记得,当时少爷的那些同学和他那位留着三绺老师,哦。。。,对了,叫什么孔老夫子的,还不停的向老爷恭贺,说什么贺喜少爷连中两元等等的。拐伯不知道这些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化人说的什么连中两元是什么意思,但他在旁边看到老爷笑得见牙不见齿的,自己也不由在一旁偷着乐。但让他更乐的是,那一天,拐伯吃到了他平生最好吃的一餐饭,虽然当然是剩饭,但都足够他回味很久了。什么海参鲍鱼,龙虾翅肚,这些在他那个穷乡下只是传说中的菜肴,后来他们收拾时可谓堆积如山。拐伯心想,老爷虽然富有却也是出身穷苦,平时一向都很节俭的,那天他如此罕见的铺张,可见少爷中了什么会。。。会元,他是多少的高兴哦。那几天我们这些下人吃得多开心啊!绝对是平生最丰盛的一次呀,拐伯记得,那一天的剩菜,他们这些下人几乎是开足了马力的狂吃,毕竟这么好的菜不是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后来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他们才心满意足的清理宴席,收拾碗筷。
“唉,那一天,简直是天堂上的日子啊!”拐伯现在已不由感叹出了声,他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他这种自小就捱饿的穷孩子,他只有个很朴素的想法,如果他能吃得饱就很满足了,如果能吃得好点,那简直就是天堂了。不但是拐伯,这也许是天朝很多朴实的很容易满足的农民的普遍想法吧。
拐伯不由又咂了咂嘴,忽然发觉自己那干瘪肚子似乎更饿了。他不由向少爷瞧了瞧,不知何时,少爷却又已拿起本不知什么书正看得津津有味,浑不象肚子饿了的样子,拐伯不觉一阵惭愧,自己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连少爷好象都未饿,怎么自己竟然会觉得饿了呢?
拐伯挺了挺肚子,假装自己刚饱餐了一顿鲍参翅肚了样子,脸上还浮起了一丝酒足饭饱般的微笑,又继续回忆起来。
唉,要不是老爷后来被奸人陷害,自己应该还会吃过很多次鲍参翅肚吧,这时拐伯忽然叹了口气,脸上居然起股恨意,在茅房顶空隙中透过的几缕光线的晃动下,他这股恨意让他那枯槁肌黄的脸看起来有几分狰狞。
也许这种神色,出现在一位行将就木,看惯风云的老人脸上是很不协调也很不正常的。但能让这个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视如无物的老人这么恨的,当然不会是后来他吃不到鲍参翅肚了,而是因为那个险恶的人和他那恶毒的人性。
拐伯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他的老爷、少爷,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恨那位所谓恶人。正所谓,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使卑微如拐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道理都是同样的。
拐伯头上忽然冒出了一阵冷汗,因为这时他的心忽然变得冷嗖嗖的,甚至比他那晚在知县门口接老爷回来时,那铺天盖地的宇宙历2002年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更冷。
那是少爷喜宴后的第二天,当天下了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但让李家上上下下心更冷的,却是发生在老爷身上的那件飞来横祸。
那天晚饭后,拐伯搭老爷去赴知县大人的一次邀约,他并不知他们之间谈些什么,只不过以为是一次平常的会晤。谁知他在外面这一等就是五个小时,当他再次见到老爷时,他就象条狗般被人扔了出来,全身上下血淋淋的,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地方。
拐伯用马车将老爷拉回去后,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最终只捱到第二天凌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去了,少爷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有多大,昨天才中了会元,今天就遭遇这样的变故,他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哦,这样的大喜大悲他怎么禁受得了。拐伯想到这里,感觉自己的眼睛变得有点湿湿的。
在老爷离世前的那天夜里,他们断断续续的了解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大概,原来那个知县王大人,一直觊觎老爷的财产,经常有意无意的暗示老爷要给他点好处,否则就要给老爷小鞋穿。可是老爷这人一贯刚直,又那会做那些行贿的事。总以为自己生意、做人都行得正站得直,而且他一贯看不起这位靠行贿、擦鞋而当了官的这位知县,平时都不屑与他为伍,又那会给这种人送什么礼呢?
老爷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平时我们这些下人自己或家里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很大方的周济的,但对于那种贪官,他不但不会赠予分毫,而且有一次还当着许多人的脸,将这位不要面皮,公然伸手要钱的贪官狠狠的斥责了一番。如此也就算了,老爷那次可能真的是太气愤了,他居然还将这位贪官为恶乡里,贪污受贿的事上报给了这位知县的上司,老爷为人一世英明,特别是在做生意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却怎么在这种事上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呢?现在的官那一个不是靠级级行贿上去的呢?知府要不是吃了这个知县的钱,怎么会将这个为害乡里,欺压勒索百姓的黑社会泼皮头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提为知县呢?而老爷现在却天真的到知府那里告这个知县行贿受贿,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老爷在各方面都出类拨萃,偏生在这方面却还心生侥幸,殊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道理,现在就是连三岁小儿都懂的。
老爷一生不勾结官府,能打拼出当时一片家业,普天之下都已算一个奇迹了。但现在到更大的贪官面前靠贪官,现在的官府已经腐败到如此田地,民又怎能与官斗,老爷又岂会有幸理?
拐伯越想越气,忽然右手狠狠一掌拍在自己大腿上,力道之大,令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又老又残又饿的老人之手。
果不其然,很快那位扶植王泼皮上位的知府大人就以老爷越级上访,不符诉讼程序为由,将老爷上告一案拨回给王泼皮审核。
这不是开玩笑吗这?这天底下还有如此腐败荒唐的官府吗?被告的人审核告状的人,这案件还用审吗?
这时拐伯的面上忽然现出一丝凄然的笑意,这丝笑意似乎让他那枯瘦的脸看上去没有那么狰狞了,却仿佛更让人害怕,因为这笑意中似乎包含着更多的仇恨。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了。
这件案件被转批回来的当晚,那知县小人果然阴险之极,他怕公然拘捕老爷会转移财产,为了达到全盘并吞的目的。竟假惺惺的派人向老爷邀约,道自己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诚心接受老爷的监督、批评,以后将积极退赃拒贿,为表感激悔改之意,特请老爷到其府上小酌几杯。。。
那时知道这消息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王知县一定是在扯谎,这人一贯品行恶劣,怎么一下就转了性了呢?岂不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吃肉的老虎怎么可能改吃素呢?但老爷却很信仰少爷的老师的孔老夫子那一套,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反过来批评大家太固执,把人性看得太卑劣了。
看来有文化是好的,但如果将书本的东西教条化了,不懂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完全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的话,就是孔夫子这个大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在现实中有时也不定对哦。拐伯似懂非懂的想着。
果真不幸被大家言中,老爷一进县衙,那个泼皮县长就露出了真面目。强迫老爷在他们拟好的莫须有罪状上签押。道老爷贩卖私盐,行贿官员,支持乱党,意图造反。。。罪大恶极,须将其财产充公。。。
这不是屈得就屈吗?老爷生意虽多,但八杆子都跟什么卖盐沾不上边呀。支持乱党,老爷这人一生谨小慎微,除了生意上的必要应酬,大门都不多出一步,何来什么乱党朋友呢?最离谱的还是什么行贿官员,老爷就是不愿也不想行贿才遭了这罪呀,现在却反倒成了他的罪名,这真是天大的讽刺阿!通篇也许就那句财产充公才是最靠谱的,他们罗列了这么多罪名,无非就是为了吞并老爷的财产而已。
可怜老爷当然不肯认罪,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还趁老爷昏迷时,硬将他手指按到罪状上按了指模,就这样当他认了罪。这世上还有公理吗?老爷一生光明磊落,老来却要受此等屈辱,一口气那能咽得下去,再加上又受到那些人的严刑拷打,两相折磨之下,终是捱不过第二天早上,就含恨而终了。
第二天一早,那个泼皮县长就派人来查封了老爷的财产,最惨的是老爷所有亲属子女,男的流放到边关服苦役,女的被分配到官家当奴婢。下面的佣人,也都跑得清光了。想不到含辛茹苦才打拼下的这番家业,居然最后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要不是这事情真的发生了,想必没人会相信这世上会发生如此荒唐透顶、灭绝人性的人间惨剧。
万幸的是,第二天少爷刚好回去还拜师恩,拜访亲友了,才险险逃过此却。当他晚上回来时,就如从天堂一下子掉进地狱般,已变成一个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了。
幸亏,当时还有拐伯,一个几百人口的,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的庄园,现在就只剩下的拐伯在他身旁。而也只有拐伯,才能让他这几十年来,不至于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原来他父亲当年,为了以后能落叶归根,却还在自己的老家建有一所大宅,而且里面还收藏有不少这些年来他购置下来价值连城的珍宝古玩,为了不走漏风声引来盗贼,这个大宅平时也就只有忠心耿耿,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拐伯有时回去打点看顾。其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妻妾儿女都无一人知晓。或许他想等到衣锦还乡的那一天才给他们一个惊喜吧,谁知他却终于没能等到那一天了。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他是没有看错的,那就是拐伯的人品,李中吾的父亲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也幸亏还有拐伯这样一个如此忠心如此重义的人,在那天后带他回到他父亲在老家建的宅第中,并靠着家里的那些珍玩古董,才让他过了这几十年虽然不耕不种不乞不讨,却至少能做到衣食无忧的日子。
这时拐伯脸上也浮上了层淡淡的笑意,不知是他想起自己这个卑微的人,终于对当年太老爷将他这个被人遗弃在路边,饿得奄奄一息的残疾儿的拾养救命之恩有了点回报。还是想起少爷平时跟他说起的那些宫闱情仇,诸侯争霸的有趣故事。
原来当年李中吾跟着拐伯逃离当地回到父亲的老家后,他一个舞象之年的少年,年纪轻轻就遭逢家庭如此变故,身心如何禁受得起。回来后不久就大病了一场,要不是有拐伯当时在一旁无微不至的照顾,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不过身病好医,心病却是再医不好了。自此后,他就心性大变,对什么官场仕途,竟已再提不起丁点兴趣。就连世间琐事,竟都觉得多余了。每天爱做的,也只是读书写书而已,父亲的惨遭横祸实在对他刺激太大,人性居然可以恶毒到如此程度,他要钻研出一本有关人性丑陋的作品,看看人的心能黑到什么程度。正因如此,现在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也就只有一个拐伯。
而拐伯,也的确值得他信任,因为这三十多年来,他除了读书写书,剩下的家务、杂工都让拐伯承包了,虽然他要求不太高,衣服可以三个月不换,吃饭有个烧饼也可,最多他就是闲暇时,或看书写书累了时,跟拐伯聊一下书里的趣事,或自己大作的精深,虽然也不知拐伯能不能听得懂,只是经常咧着个口嘿嘿地傻笑。但对于他这个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来说,这已经算是生活中一种难得的乐趣了。毕竟身边还有个这么忠实的听众。
但李中吾现在大作完成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闭关”也许时间真的有点太长了,不但拐伯早老得没牙了,原来自己也已一把年纪了。最惨的是父亲的那些家产都给他“挥霍一空”了,大作是完成了,但晚餐却没着落了。
李中吾现在已饿得看不下书了,他放下书本,心里颇是感慨了一番,他好象现在才意识到,他欠拐伯的实在太多了,拐伯如此无偿的照顾了他几十年,他现在居然连请拐伯吃个烧饼都请不起,这实在是让人于心难安呀,他不由有点歉疚的向拐伯坐的地方看去。却见拐伯坐的地方竟是空空如也,那有一个人在。
李中吾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已跟拐伯相处了几十年了,拐伯的性格他那有不知,除非有什么非离开不可的事,拐伯就当他是鸟巢中的小雏鸟,而拐伯就象只尽责的母鸟,是断不会贸然离开他的。而两人这几十年的相处下来,李中吾也已对拐伯有了种似乎比对父亲都更深厚的感情。
他匆忙起身,跑出家门四处呼喊张望,但四野茫茫,除了风雪呼号,那有拐伯的影子,在这样的风雪天气,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到野外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李中吾心里忽然涌起股不祥的预感,这感觉太可怕了,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他的额头居然沁出了一层汗水。
但现在想什么都是多余的,李中吾甚至已不敢再想,他只象只发狂的野狗般,四处呼号着搜寻着,直跑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他都没有找到拐伯,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了自己的那间草庐,期待着有奇迹发生,但终究,拐伯没有回来。
那一晚,李中吾没有整晚都没有睡,因为他哭了一晚,除了父亲死的那次,他还是第二次哭得那么伤心。
因为他知道,拐伯没有回来就是回不来了,否则他爬都会爬回来。他已经猜到拐伯为什么当时要离开他出去了,这让他哭得更伤心!
果然,第二天早上,当李中吾在昏昏沉沉中被人吵醒的时候,他开门时就见到了拐伯那僵硬的尸体,那是早起的邻居们在很远的地方发现的,跟他僵硬的身体一样僵硬的,是他瘦骨嶙峋的手上拿着的两个烧饼,还有他那脸上已被冻结了的僵硬的笑容。也许他临死时还在想,终于能给少爷找到晚餐了,终于可以庆祝一下少爷的大作完成了。所以,他去得很安祥,很欣慰。
看到这情景,连送他回来的邻里都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谁会想到,在这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卑微的老人身上,竟然会蕴含着这么伟大的人格呢!
但在他们伤感和愤怒的泪眼中,他们却居然只看到,李中吾只是冷漠的叫他们回去,甚至连感谢都不多一句。最后,这些热心的乡里,也只好咒骂着李中吾没良心,那样的天气还叫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去帮自己买东西,或者又叫嚷了几句他是个疯子诸如此类的话,怏怏然的散去了。
他们却不知道,李中吾的心在昨晚已经被自己的内疚冻得僵硬了,他的眼泪也已经流干了。现在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留待以后,当夜半梦回时,再象一只受伤的动物般,慢慢舔干自己伤口上的血而已。
但他现在必须做的,却是要将拐伯下葬,刚才在众人面前被误解奚落,他现在是断不能向别人开口借钱的了,何况以他的性格,就算没有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向人开口借钱都是件颇为踌躇的事。
环顾四周,自己剩下的,除了那本刚完成的《厚黑学》,满室唯有堆积如山的书籍矣。这些书籍花了他几十年时间才搜集得来,都是他心爱之物,如是平时,任是别人出再多价钱,他都是不肯随便转让的,但自己为之呕心呖血的作品刚完成,就遭遇如此变故,心里大感挫折,只觉自己奉为珍宝之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值钱。至少现在他最需要就不是书籍,而是能让拐伯能体面点下葬的一口棺椁
。
而要购买棺椁就需要钱,现在他能拿什么来换钱,举目看去,他这茅庐里除了书之外就那几件连收破旧佬可能都不要的破桌敝衣,李中吾不禁心里暗叹,想不到自己居然已沦落到如此田地,心里又是挣扎了一番,终于还是下定了主意。
接下来不久,他在屋边小溪胡乱喝了几口水充饥,修理了下实在太野人的胡子,找了件还算好点的衣服穿上,比较象个正常人之后,就背个破麻袋,装着自己认为不太合用的数十本书,到了附近的市集上,混杂在那些小摊小贩旁边,摆起了地摊。
可怜这么个几十年大门不出的人又如何会做生意呢?他用 一张烂席摆下了自己的那几十本书后,就垂着个头在那里算手指了。偶尔有几个无聊之人来看了看,他却将自己的头垂得更低了,就象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别人看他这样,本来想问下价的,但这世上那有这么怕羞的店主。所以当李中吾终于在摆摊半个小时后,鼓起最大的勇气抬起头的时候,他发觉他售卖的书已不见了一半。铜板却是一个都没。
还好有几个良心好点的,认为窃书不算偷,或者也象李中吾那般穷,或者良心有点发现,终究还是掉下了几个烂苹果呀咬过的馒头。当然,他们不知,现在这些东西对于李中吾来说,不异于珍馐美味,在其他小贩喊得天价响的叫卖声中,在旁人诧异的眼光中,李中吾终于填饱了肚子。但没有铜板,拐伯还是不能下葬的,没办法,李中吾还是要继续叫卖下去。
他还是垂着他的头,这时忽然旁边一阵惊呼,旁边的小贩象见了鬼一般在惊呼:“镇关西来了,走鬼!”然后是一阵鸡飞狗走,惊惶四散的噪音。李中吾大惊抬头,愕然发觉刚才还熙熙攘攘的市集突然间已变得冷冷清清,刚才他身边的那些小摊不知何时已走得一干两净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李中吾还未回过头来,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肚腩,他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一脸横肉,歪戴着一顶大檐帽的壮汉站在他面前,正用一双醉醺醺的眼睛斜睨着他,后面还跟着几个喽罗般的手下,个个杀气腾腾的样子。
李中吾这种几乎大辈子没出过门人那见过这种阵势,他本来就不擅言辞,现在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大盖帽似乎觉得他大不敬,突然气乎乎的一脚将的剩下的书连书带席都踢得四散飞去,口中嚷道,“你个死要饭的,见到我居然都不走,你是不是很嚣张?”
李中吾却不明白为什么见了他为什么要走,虽然这人的尊容未达到他见了就想亲上一口的地步,但也不至于一见就要走呀?他现在实在不知要如何回答,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只能很无辜的半张着口。
那盖帽大汉踢了他书,却见这人好象并不如何作怒,脸部又是如此一个表情,却也颇有点有气无处使之感。只能气哼哼的道,“我就是镇关西郑屠,渭州府城管大队大队长,这里的市场都归我管,你知道吗?在我的地头摆摊,没我的批准就是乱摆摊,明白吗?。。。”
他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中气十足,但李中吾却如何知道这些东东,他只懂天大地大,莫不是百姓土地,摆个小摊而已,居然都要被批准。他实在不懂这些,所以他只能继续沉默。
那个城管队长郑屠看他那副瘦骨啦叽衣衫褴褛的样子,看来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可能也觉无趣,这时高嚷了一声,“乱排摊,影响市容,将他的书没收充公,扯呼。”
李中吾只觉得他话音未落,这股人速度之快,几乎在他口都还未来得及合上的的当儿,这帮人已将他剩下的书收拾清光并走得没影了。
。。。。。。
李中吾都不知如何形容现在自己的感受,不过不论如何,他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做事的效率,这种效率绝对是久经磨练,工多手熟的结果。
不用顶了,你要看来我家看吧呵呵,准备写到30万字,至少两个月吧。有点辛苦的,不在这里发了,俺想挣钱哦,当然能不能挣到是另外回事,要写几十万字,我至少佩服俺有点毅力的,嘿嘿。。。
俺很差钱滴。。
少年多梦,人皆如此,即使有些梦是很荒唐和很好笑的,也属正常。秦烩少时虽也象许多同龄人般喜做各种各样奇怪的梦。但他出身寒微且命运多舛,却难得的较之一般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和现实。
从小他就明白,象他这种出身的,不比那些含着金钥匙出身,自小家里人就已经给他们铺好了金光大道的富贵家庭子女。甚至比那些虽然贫穷但至少双亲健在、普通正常的家庭也是远比不上。因为他们的子女至少不会象他这样,自小就被人讥讽为“野种”
如果说出生于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对于秦烩来说,唯一还有点好处的话,那就是这种经历让他更早熟,更清楚的认识到只有自己长大以后能出人头地,才能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并得到别人的敬畏。
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读书科举一途了。所以,自小秦烩就比班上所有人读书都更努力,再加上他天生聪颖,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在17岁时就高中状元,自誉为“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当然后来有人考证,封川县文德乡(属现在封开县)出了个“岭南首魁状元”莫宣卿,高中时也只有17岁,却比秦烩迟出生了一天,他才应是“史上最年轻的状元”,因本文非是严肃学术论文,这里就不作甄别了。
且说秦烩高中状元后,以为这下终于时来运转,一抒抱负了。谁知皇帝除了在他状元及第那天在皇宫大殿上设宴并赐了他一杯酒后,就好象将他忘记得一干两净了一般。只让他任了个翰林院修撰的闲职,顾名思义,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干点啥的了吧?如果谁嫌自己的头发太浓密眼睛太明亮,那这份工作还算得上是不错的选择。具体点说,就是修正或考证“日暮苍山兰舟小 本无落霞缀清泉 去年叶落缘分定 死水微漾人却亡 ”之类的诗句究竟是李黑写的还是李白写的,并是否在这首诗中预言了日本去死,小泉定亡的谶语等无厘头的工作。
这还不算,这工作竟然一做还做了三十年,秦烩不但那一头浓密的热带雨林都熬成地中海了,
称呼上还多了个“三朝元老”的后缀,如果说这三十年时间里有了点成绩的话,就是在任职第28个年头的时候被现在的晕宗皇帝赐了个“内阁中书大学士”的虚衔,聊算个精神安慰吧。
“这王朝的皇帝都是些窝囊废,想不到自己堂堂一代状元,竟沦落到与鼠蚁为伴的下场,穷苦百姓培养一个人才容易吗?就这样给糟蹋了,何况自己。。。”仕途暗淡郁郁不得志,秦烩不免经常自怜自艾一番,特别是想到自己那倍加凄惨的童年时,几乎都不忍再想下去,但心中的怨气却又更添了几分。
这晚秦烩膳后正在厅里闲坐,这时忽有门僮来报,道有一旧友求见,秦烩不知是谁,挥手让门僮过去叫他进来,自已旋也整束衣冠,出去迎接。刚转过影壁,只见迎面而来的,赫然竟是小时学友,已有三十多年未见的―李中吾是也。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这李中吾为何许人,其实说到他的著作,应该是市井文盲,都会略有所闻的了,不错,他就是著述有旷世奇书《厚黑学》的那个一代怪才李中吾是也。
李中吾小时跟秦烩少年同学,文采风流可谓一时瑜亮,不分轩轾。本来专心于功名的话,那一年的南京状元是他的而非秦烩的也说不定,但他偏生天生一副傲骨,为人清高自持。眼见官场腐败横行,官员贿赂成风,他一片仕途之心,不由早早的冷了下来。就在中了会元后不久,他就抛下了孔孟之书,归隐田园,醉心于研究社会百态,著书立说了。
秦烩跟他多年不见,关于他的状况也只是略有所闻。他在内心中虽对李中吾那种人生哲学不以为然,但毕竟同窗有年,且当年都是一代才子,心里不免有点惺惺相惜之心。何况两人多年不见,自己刚好今晚也满腹心事,有朋自远方来,煮酒论下英雄,不亦乐乎。于是两人略作寒暄,秦烩就命下人摆下酒席,两人下坐,不免一番觥筹交错。
几杯下肚,秦烩已有了几番酒意,今天能见旧友,心中自是高兴,但想想自己至今犹自潦倒,又是心生感触,不由长叹了口气。
李中吾正跟他喝得开心,正见他突然叹气,心下不解,讶然问道:“秦兄正喝得高兴,何故突然叹气呢?”
秦烩本是城府极深、内向寡言之人,平时心事都放心里,断不会随便跟别人提起的。但一来今天开心喝多了几杯;二来李中吾又非政界同僚,不虞酒后失言给传出去误事。最大的原因是,他现在的确是很想找个人倾诉下,难得碰到个如此适合的听众。于是在又长叹一声后,就将这些年来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一股脑儿的向李中吾全倾诉了出来。
毕竟几十年的事了,即使秦烩已尽量说得简单扼要,还是花了差不多一支香的时间才好不容易说完。对秦烩来说,这可能是他平生以来,跟别人说过最多话的一次了。几乎是说得气喘吁吁、咳嗽连连,虽然说得辛苦,但将心里的苦水都倒了出来后,秦烩竟然感到心里有一种难得的舒畅感,心情好象也平和了许多。也难怪,象他这种平时做人总带着个面具,三闷棍都打不出一个响屁,除了尔虞我诈几乎没一个真心朋友的人,是很能会有这种畅尽所言的快感的。
这时秦烩拿眼光向李中吾瞧去,那眼神任谁都看得出,秦烩现在多希望从对方的口中听到些安慰及勉励的话,一个平时没什么朋友的人,也许有时内心里是特别的需要朋友的。
却见李中吾脸上似笑非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却口不作声,只是一味不停地向他劝酒,也不知他究竟有没有听清楚刚才秦烩在说什么,真是浪费了秦烩那好一番表情。
秦烩心下不乐,却又不好说什么,他本就是那种闷骚之人,这下又恢复了那种阴沉沉的的脸容,寻思。“自己真是自作多情,对牛弹琴了。”现在他只想这李中吾快点喝完酒,好结束这让他尴尬的场面。他却未想到原来自己连李中吾为何来到此地,为什么事来找他都未曾问过,只是大家一坐下就顾着向别人吐苦水。
原来这李中吾今天来找秦烩,内里却果真是有一番情由的。
且说当年李中吾归隐田园后,每日专注的,只是如何能写出本有关人性恶劣方面的专著,特别是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的发家史及统治史。人可能真是种奇怪的动物,象他这种无心于功名无心于政界发展的人,却偏偏在做学问方面对政治最感兴趣。于是在著书立说方面,也拣了这方面的主题来做。
这数十年来,他为了完成这方面的研究,那真可谓是穷经究典、呕心沥血矣。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三个月前,他那本花费了三十多年心血的巨著《厚黑学》终于问世了,这让他欣慰无比。但让他感到凄凉的是,为了写成这本书,他也将祖宗留下的,原本还算殷实的一份家产,挥霍了个一干两净。
也难怪,象他这种四肢不勤,大门不出,半年都不刮一次胡子,一年都不冲一次凉,身上那股咸鱼味连方圆五里的邻居都能闻到,除了看书就是写书的人。别人除了叫他“SB”,精神病之类,又还能叫他什么呢?更不幸的是,到李中吾大作完成时,他才仿佛发觉自己已经是身无分文了,原来祖宗留下的忒多珍玩古董。。。反正所有能给他拿来换钱的东西都早给他典当清光了。他现在除了一间茅庐和生活必需的一些台台凳凳,可说是,穷得只剩下书,因为不夸张点说,他那间烂房里几乎能塞得下的地方都塞满了书,他每次出入自己那间房子都可称得上是进行了一次体育运动。因为那书多得只能让他跳过去或侧着身慢慢地钻过去。
但李中吾现在才深切体会到,他小时候给私塾里那些教科书洗脑洗得有多厉害,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原来统统都不过是忽悠死人不包赔的歪理谬论。他终于切身体会到了那位人如其名身材高大的邓大平同志那句“实践是体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多么的正确。原来,挣钱才是硬道理,其他统统都是扯蛋。就象李中吾当时刚刚完成自己的巨著《厚黑学》时,当最初的喜极而泣过后,他发觉自己又要悲极而泣了。原来下一餐的饭钱没着落了。上天偏偏就这么捉弄人,连他想买个烧饼来庆贺数十年的心血结晶的钱竟然都没给他留下来。因为在他刚完成巨著后,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自己居然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有了。
李中吾悠悠地长叹了一口气,高呼了一声“拐伯”,很快就象变戏法一般,他那乱蓬蓬的书堆中忽然伸出一只更乱蓬蓬那头乱草般的头发跟他有得一比的脑袋,在这乌黑的屋子里就象带了个伪装,眼力差点都看不出来。但李中吾早就在暗无天日的烂房子练就了夜猫般的好眼力,他甚至连“拐伯”还剩下多少只蛀牙都瞧得一清两楚。
这时他心中存着最后一丝侥幸的向那位叫“拐伯”的道,“你身上还有一个铜板吗。”果不其然,他从拐伯那里得到的,是一抹和他一样绝望的眼神,还有“咕噜”的一声回答。这回答其实并非来自于拐伯口中,而是来自于肚子中,李中吾甚至都搞不清楚这一声“饱噎”究竟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拐伯。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李中吾不算很穷呀,至少都还有下人使唤,拐伯是他的下人没错,但如果这个下人有地方去,应该也象其他他曾经拥有的999个下人般走个清光了。
连李中吾都不知道,这个叫拐伯的已经在他家呆多久了,可能连他爸爸都不知道,因为他爸爸未出生时,这拐伯就已经在他家当男佣了。反正至少都是他李家的三朝元老了。这老头也不知有多少年纪了,老得连牙齿都没有了,所以李中吾的眼力好不好不知道,但他不用瞧就知道拐伯有多少颗蛀牙倒是事实,因为不用瞧,他都清楚拐伯连一颗牙齿都没有了。
但李中吾却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自小就知道他因为左脚有点跛,所以大家都叫他拐伯,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因为在李中吾印象中,从来就没有见过他有什么家人来探过他,相信也跟现在的李中吾一样,早就是个孤家寡人了。
这样一个又老又跛的人,除了跟着他这个自小他就服侍到大的“少爷”外,他还有什么地方好去,还能靠什么谋生呢?至少跟着李中吾虽然没什么好吃好住的,今天早上大少爷身上还有两个铜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还能买了两个烧饼,各自分了一个吃。
至少大少爷都算对他不薄,甚至已真正达到有福有享,有难同当的高尚境界,这不,刚才他饿得肚子打咕噜时,大少爷都跟他一起担当了。
这世上到那里能找到这么好的主人哟,所以虽然少爷都半年不出柴门,但一日三餐(假如运气好的话还是有的,而不象今天早上到现在吃晚饭时候了才只吃了个烧饼)的工作,拐伯还是任劳任怨连用拐杖都感觉有点拐不起来却全部承担了下来。
能支撑他这样做下去的,除了少爷跟他同睡一间房同吃一块饼的一片良心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拐伯从小就没读过书,完全睁眼瞎一个。所以自小就很敬重有文化的人。少爷当然是个很有文化的人,自小就天资过人傲视同侪。拐伯还清楚的记得,少爷还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时候全部拿了第一。记得当时老爷在少爷考了会试第一的时候,还在庄园里摆了九十九台筵席,当时真是来宾如云啊!唉,当时老爷的庄园多大啊,虽然摆了这么多台的酒席,却不过也只占老爷这庄园中的小小一角罢了。想到这里,拐伯不由在心里暗叹了一声。
他还记得,当时少爷的那些同学和他那位留着三绺老师,哦。。。,对了,叫什么孔老夫子的,还不停的向老爷恭贺,说什么贺喜少爷连中两元等等的。拐伯不知道这些满口之乎者也的文化人说的什么连中两元是什么意思,但他在旁边看到老爷笑得见牙不见齿的,自己也不由在一旁偷着乐。但让他更乐的是,那一天,拐伯吃到了他平生最好吃的一餐饭,虽然当然是剩饭,但都足够他回味很久了。什么海参鲍鱼,龙虾翅肚,这些在他那个穷乡下只是传说中的菜肴,后来他们收拾时可谓堆积如山。拐伯心想,老爷虽然富有却也是出身穷苦,平时一向都很节俭的,那天他如此罕见的铺张,可见少爷中了什么会。。。会元,他是多少的高兴哦。那几天我们这些下人吃得多开心啊!绝对是平生最丰盛的一次呀,拐伯记得,那一天的剩菜,他们这些下人几乎是开足了马力的狂吃,毕竟这么好的菜不是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后来实在是吃不下去了,他们才心满意足的清理宴席,收拾碗筷。
“唉,那一天,简直是天堂上的日子啊!”拐伯现在已不由感叹出了声,他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他这种自小就捱饿的穷孩子,他只有个很朴素的想法,如果他能吃得饱就很满足了,如果能吃得好点,那简直就是天堂了。不但是拐伯,这也许是天朝很多朴实的很容易满足的农民的普遍想法吧。
拐伯不由又咂了咂嘴,忽然发觉自己那干瘪肚子似乎更饿了。他不由向少爷瞧了瞧,不知何时,少爷却又已拿起本不知什么书正看得津津有味,浑不象肚子饿了的样子,拐伯不觉一阵惭愧,自己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连少爷好象都未饿,怎么自己竟然会觉得饿了呢?
拐伯挺了挺肚子,假装自己刚饱餐了一顿鲍参翅肚了样子,脸上还浮起了一丝酒足饭饱般的微笑,又继续回忆起来。
唉,要不是老爷后来被奸人陷害,自己应该还会吃过很多次鲍参翅肚吧,这时拐伯忽然叹了口气,脸上居然起股恨意,在茅房顶空隙中透过的几缕光线的晃动下,他这股恨意让他那枯槁肌黄的脸看起来有几分狰狞。
也许这种神色,出现在一位行将就木,看惯风云的老人脸上是很不协调也很不正常的。但能让这个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视如无物的老人这么恨的,当然不会是后来他吃不到鲍参翅肚了,而是因为那个险恶的人和他那恶毒的人性。
拐伯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他的老爷、少爷,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恨那位所谓恶人。正所谓,人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使卑微如拐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个道理都是同样的。
拐伯头上忽然冒出了一阵冷汗,因为这时他的心忽然变得冷嗖嗖的,甚至比他那晚在知县门口接老爷回来时,那铺天盖地的宇宙历2002年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更冷。
那是少爷喜宴后的第二天,当天下了有史以来最冷的第一场雪。但让李家上上下下心更冷的,却是发生在老爷身上的那件飞来横祸。
那天晚饭后,拐伯搭老爷去赴知县大人的一次邀约,他并不知他们之间谈些什么,只不过以为是一次平常的会晤。谁知他在外面这一等就是五个小时,当他再次见到老爷时,他就象条狗般被人扔了出来,全身上下血淋淋的,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地方。
拐伯用马车将老爷拉回去后,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最终只捱到第二天凌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这样去了,少爷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有多大,昨天才中了会元,今天就遭遇这样的变故,他才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哦,这样的大喜大悲他怎么禁受得了。拐伯想到这里,感觉自己的眼睛变得有点湿湿的。
在老爷离世前的那天夜里,他们断断续续的了解了这件事情的一个大概,原来那个知县王大人,一直觊觎老爷的财产,经常有意无意的暗示老爷要给他点好处,否则就要给老爷小鞋穿。可是老爷这人一贯刚直,又那会做那些行贿的事。总以为自己生意、做人都行得正站得直,而且他一贯看不起这位靠行贿、擦鞋而当了官的这位知县,平时都不屑与他为伍,又那会给这种人送什么礼呢?
老爷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平时我们这些下人自己或家里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很大方的周济的,但对于那种贪官,他不但不会赠予分毫,而且有一次还当着许多人的脸,将这位不要面皮,公然伸手要钱的贪官狠狠的斥责了一番。如此也就算了,老爷那次可能真的是太气愤了,他居然还将这位贪官为恶乡里,贪污受贿的事上报给了这位知县的上司,老爷为人一世英明,特别是在做生意方面简直是个天才,却怎么在这种事上会糊涂到这种地步呢?现在的官那一个不是靠级级行贿上去的呢?知府要不是吃了这个知县的钱,怎么会将这个为害乡里,欺压勒索百姓的黑社会泼皮头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提为知县呢?而老爷现在却天真的到知府那里告这个知县行贿受贿,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老爷在各方面都出类拨萃,偏生在这方面却还心生侥幸,殊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道理,现在就是连三岁小儿都懂的。
老爷一生不勾结官府,能打拼出当时一片家业,普天之下都已算一个奇迹了。但现在到更大的贪官面前靠贪官,现在的官府已经腐败到如此田地,民又怎能与官斗,老爷又岂会有幸理?
拐伯越想越气,忽然右手狠狠一掌拍在自己大腿上,力道之大,令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又老又残又饿的老人之手。
果不其然,很快那位扶植王泼皮上位的知府大人就以老爷越级上访,不符诉讼程序为由,将老爷上告一案拨回给王泼皮审核。
这不是开玩笑吗这?这天底下还有如此腐败荒唐的官府吗?被告的人审核告状的人,这案件还用审吗?
这时拐伯的面上忽然现出一丝凄然的笑意,这丝笑意似乎让他那枯瘦的脸看上去没有那么狰狞了,却仿佛更让人害怕,因为这笑意中似乎包含着更多的仇恨。
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了。
这件案件被转批回来的当晚,那知县小人果然阴险之极,他怕公然拘捕老爷会转移财产,为了达到全盘并吞的目的。竟假惺惺的派人向老爷邀约,道自己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诚心接受老爷的监督、批评,以后将积极退赃拒贿,为表感激悔改之意,特请老爷到其府上小酌几杯。。。
那时知道这消息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王知县一定是在扯谎,这人一贯品行恶劣,怎么一下就转了性了呢?岂不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吃肉的老虎怎么可能改吃素呢?但老爷却很信仰少爷的老师的孔老夫子那一套,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反过来批评大家太固执,把人性看得太卑劣了。
看来有文化是好的,但如果将书本的东西教条化了,不懂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完全照本宣科、生搬硬套的话,就是孔夫子这个大的知识分子的东西,在现实中有时也不定对哦。拐伯似懂非懂的想着。
果真不幸被大家言中,老爷一进县衙,那个泼皮县长就露出了真面目。强迫老爷在他们拟好的莫须有罪状上签押。道老爷贩卖私盐,行贿官员,支持乱党,意图造反。。。罪大恶极,须将其财产充公。。。
这不是屈得就屈吗?老爷生意虽多,但八杆子都跟什么卖盐沾不上边呀。支持乱党,老爷这人一生谨小慎微,除了生意上的必要应酬,大门都不多出一步,何来什么乱党朋友呢?最离谱的还是什么行贿官员,老爷就是不愿也不想行贿才遭了这罪呀,现在却反倒成了他的罪名,这真是天大的讽刺阿!通篇也许就那句财产充公才是最靠谱的,他们罗列了这么多罪名,无非就是为了吞并老爷的财产而已。
可怜老爷当然不肯认罪,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他们还趁老爷昏迷时,硬将他手指按到罪状上按了指模,就这样当他认了罪。这世上还有公理吗?老爷一生光明磊落,老来却要受此等屈辱,一口气那能咽得下去,再加上又受到那些人的严刑拷打,两相折磨之下,终是捱不过第二天早上,就含恨而终了。
第二天一早,那个泼皮县长就派人来查封了老爷的财产,最惨的是老爷所有亲属子女,男的流放到边关服苦役,女的被分配到官家当奴婢。下面的佣人,也都跑得清光了。想不到含辛茹苦才打拼下的这番家业,居然最后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要不是这事情真的发生了,想必没人会相信这世上会发生如此荒唐透顶、灭绝人性的人间惨剧。
万幸的是,第二天少爷刚好回去还拜师恩,拜访亲友了,才险险逃过此却。当他晚上回来时,就如从天堂一下子掉进地狱般,已变成一个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了。
幸亏,当时还有拐伯,一个几百人口的,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的庄园,现在就只剩下的拐伯在他身旁。而也只有拐伯,才能让他这几十年来,不至于身无分文,无家可归。
原来他父亲当年,为了以后能落叶归根,却还在自己的老家建有一所大宅,而且里面还收藏有不少这些年来他购置下来价值连城的珍宝古玩,为了不走漏风声引来盗贼,这个大宅平时也就只有忠心耿耿,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拐伯有时回去打点看顾。其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妻妾儿女都无一人知晓。或许他想等到衣锦还乡的那一天才给他们一个惊喜吧,谁知他却终于没能等到那一天了。
不过至少有一件事他是没有看错的,那就是拐伯的人品,李中吾的父亲是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也幸亏还有拐伯这样一个如此忠心如此重义的人,在那天后带他回到他父亲在老家建的宅第中,并靠着家里的那些珍玩古董,才让他过了这几十年虽然不耕不种不乞不讨,却至少能做到衣食无忧的日子。
这时拐伯脸上也浮上了层淡淡的笑意,不知是他想起自己这个卑微的人,终于对当年太老爷将他这个被人遗弃在路边,饿得奄奄一息的残疾儿的拾养救命之恩有了点回报。还是想起少爷平时跟他说起的那些宫闱情仇,诸侯争霸的有趣故事。
原来当年李中吾跟着拐伯逃离当地回到父亲的老家后,他一个舞象之年的少年,年纪轻轻就遭逢家庭如此变故,身心如何禁受得起。回来后不久就大病了一场,要不是有拐伯当时在一旁无微不至的照顾,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不过身病好医,心病却是再医不好了。自此后,他就心性大变,对什么官场仕途,竟已再提不起丁点兴趣。就连世间琐事,竟都觉得多余了。每天爱做的,也只是读书写书而已,父亲的惨遭横祸实在对他刺激太大,人性居然可以恶毒到如此程度,他要钻研出一本有关人性丑陋的作品,看看人的心能黑到什么程度。正因如此,现在他唯一能信任的人,也就只有一个拐伯。
而拐伯,也的确值得他信任,因为这三十多年来,他除了读书写书,剩下的家务、杂工都让拐伯承包了,虽然他要求不太高,衣服可以三个月不换,吃饭有个烧饼也可,最多他就是闲暇时,或看书写书累了时,跟拐伯聊一下书里的趣事,或自己大作的精深,虽然也不知拐伯能不能听得懂,只是经常咧着个口嘿嘿地傻笑。但对于他这个足不出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来说,这已经算是生活中一种难得的乐趣了。毕竟身边还有个这么忠实的听众。
但李中吾现在大作完成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自己这一“闭关”也许时间真的有点太长了,不但拐伯早老得没牙了,原来自己也已一把年纪了。最惨的是父亲的那些家产都给他“挥霍一空”了,大作是完成了,但晚餐却没着落了。
李中吾现在已饿得看不下书了,他放下书本,心里颇是感慨了一番,他好象现在才意识到,他欠拐伯的实在太多了,拐伯如此无偿的照顾了他几十年,他现在居然连请拐伯吃个烧饼都请不起,这实在是让人于心难安呀,他不由有点歉疚的向拐伯坐的地方看去。却见拐伯坐的地方竟是空空如也,那有一个人在。
李中吾这一惊非同小可,他已跟拐伯相处了几十年了,拐伯的性格他那有不知,除非有什么非离开不可的事,拐伯就当他是鸟巢中的小雏鸟,而拐伯就象只尽责的母鸟,是断不会贸然离开他的。而两人这几十年的相处下来,李中吾也已对拐伯有了种似乎比对父亲都更深厚的感情。
他匆忙起身,跑出家门四处呼喊张望,但四野茫茫,除了风雪呼号,那有拐伯的影子,在这样的风雪天气,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到野外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李中吾心里忽然涌起股不祥的预感,这感觉太可怕了,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他的额头居然沁出了一层汗水。
但现在想什么都是多余的,李中吾甚至已不敢再想,他只象只发狂的野狗般,四处呼号着搜寻着,直跑到自己实在跑不动了,他都没有找到拐伯,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了自己的那间草庐,期待着有奇迹发生,但终究,拐伯没有回来。
那一晚,李中吾没有整晚都没有睡,因为他哭了一晚,除了父亲死的那次,他还是第二次哭得那么伤心。
因为他知道,拐伯没有回来就是回不来了,否则他爬都会爬回来。他已经猜到拐伯为什么当时要离开他出去了,这让他哭得更伤心!
果然,第二天早上,当李中吾在昏昏沉沉中被人吵醒的时候,他开门时就见到了拐伯那僵硬的尸体,那是早起的邻居们在很远的地方发现的,跟他僵硬的身体一样僵硬的,是他瘦骨嶙峋的手上拿着的两个烧饼,还有他那脸上已被冻结了的僵硬的笑容。也许他临死时还在想,终于能给少爷找到晚餐了,终于可以庆祝一下少爷的大作完成了。所以,他去得很安祥,很欣慰。
看到这情景,连送他回来的邻里都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谁会想到,在这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卑微的老人身上,竟然会蕴含着这么伟大的人格呢!
但在他们伤感和愤怒的泪眼中,他们却居然只看到,李中吾只是冷漠的叫他们回去,甚至连感谢都不多一句。最后,这些热心的乡里,也只好咒骂着李中吾没良心,那样的天气还叫个年纪这么大的人去帮自己买东西,或者又叫嚷了几句他是个疯子诸如此类的话,怏怏然的散去了。
他们却不知道,李中吾的心在昨晚已经被自己的内疚冻得僵硬了,他的眼泪也已经流干了。现在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留待以后,当夜半梦回时,再象一只受伤的动物般,慢慢舔干自己伤口上的血而已。
但他现在必须做的,却是要将拐伯下葬,刚才在众人面前被误解奚落,他现在是断不能向别人开口借钱的了,何况以他的性格,就算没有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向人开口借钱都是件颇为踌躇的事。
环顾四周,自己剩下的,除了那本刚完成的《厚黑学》,满室唯有堆积如山的书籍矣。这些书籍花了他几十年时间才搜集得来,都是他心爱之物,如是平时,任是别人出再多价钱,他都是不肯随便转让的,但自己为之呕心呖血的作品刚完成,就遭遇如此变故,心里大感挫折,只觉自己奉为珍宝之物,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值钱。至少现在他最需要就不是书籍,而是能让拐伯能体面点下葬的一口棺椁
。
而要购买棺椁就需要钱,现在他能拿什么来换钱,举目看去,他这茅庐里除了书之外就那几件连收破旧佬可能都不要的破桌敝衣,李中吾不禁心里暗叹,想不到自己居然已沦落到如此田地,心里又是挣扎了一番,终于还是下定了主意。
接下来不久,他在屋边小溪胡乱喝了几口水充饥,修理了下实在太野人的胡子,找了件还算好点的衣服穿上,比较象个正常人之后,就背个破麻袋,装着自己认为不太合用的数十本书,到了附近的市集上,混杂在那些小摊小贩旁边,摆起了地摊。
可怜这么个几十年大门不出的人又如何会做生意呢?他用 一张烂席摆下了自己的那几十本书后,就垂着个头在那里算手指了。偶尔有几个无聊之人来看了看,他却将自己的头垂得更低了,就象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别人看他这样,本来想问下价的,但这世上那有这么怕羞的店主。所以当李中吾终于在摆摊半个小时后,鼓起最大的勇气抬起头的时候,他发觉他售卖的书已不见了一半。铜板却是一个都没。
还好有几个良心好点的,认为窃书不算偷,或者也象李中吾那般穷,或者良心有点发现,终究还是掉下了几个烂苹果呀咬过的馒头。当然,他们不知,现在这些东西对于李中吾来说,不异于珍馐美味,在其他小贩喊得天价响的叫卖声中,在旁人诧异的眼光中,李中吾终于填饱了肚子。但没有铜板,拐伯还是不能下葬的,没办法,李中吾还是要继续叫卖下去。
他还是垂着他的头,这时忽然旁边一阵惊呼,旁边的小贩象见了鬼一般在惊呼:“镇关西来了,走鬼!”然后是一阵鸡飞狗走,惊惶四散的噪音。李中吾大惊抬头,愕然发觉刚才还熙熙攘攘的市集突然间已变得冷冷清清,刚才他身边的那些小摊不知何时已走得一干两净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李中吾还未回过头来,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肚腩,他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满面络腮胡子,一脸横肉,歪戴着一顶大檐帽的壮汉站在他面前,正用一双醉醺醺的眼睛斜睨着他,后面还跟着几个喽罗般的手下,个个杀气腾腾的样子。
李中吾这种几乎大辈子没出过门人那见过这种阵势,他本来就不擅言辞,现在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大盖帽似乎觉得他大不敬,突然气乎乎的一脚将的剩下的书连书带席都踢得四散飞去,口中嚷道,“你个死要饭的,见到我居然都不走,你是不是很嚣张?”
李中吾却不明白为什么见了他为什么要走,虽然这人的尊容未达到他见了就想亲上一口的地步,但也不至于一见就要走呀?他现在实在不知要如何回答,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只能很无辜的半张着口。
那盖帽大汉踢了他书,却见这人好象并不如何作怒,脸部又是如此一个表情,却也颇有点有气无处使之感。只能气哼哼的道,“我就是镇关西郑屠,渭州府城管大队大队长,这里的市场都归我管,你知道吗?在我的地头摆摊,没我的批准就是乱摆摊,明白吗?。。。”
他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中气十足,但李中吾却如何知道这些东东,他只懂天大地大,莫不是百姓土地,摆个小摊而已,居然都要被批准。他实在不懂这些,所以他只能继续沉默。
那个城管队长郑屠看他那副瘦骨啦叽衣衫褴褛的样子,看来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可能也觉无趣,这时高嚷了一声,“乱排摊,影响市容,将他的书没收充公,扯呼。”
李中吾只觉得他话音未落,这股人速度之快,几乎在他口都还未来得及合上的的当儿,这帮人已将他剩下的书收拾清光并走得没影了。
。。。。。。
李中吾都不知如何形容现在自己的感受,不过不论如何,他不得不佩服这些人做事的效率,这种效率绝对是久经磨练,工多手熟的结果。
[snapback]2868898[/snapback]
不用顶了,你要看来我家看吧呵呵,准备写到30万字,至少两个月吧。有点辛苦的,不在这里发了,俺想挣钱哦,当然能不能挣到是另外回事,要写几十万字,我至少佩服俺有点毅力的,嘿嘿。。。
俺很差钱滴。。
- 注册
- 2007-04-22
- 帖子
- 5,300
- 反馈评分
- 2
- 点数
- 0
这结果不太美妙,但形势比人强,李中吾现在又能怎样呢?他感觉这些人比他乡间的黑社会更没人性,黑社会或许还能说点道理,这些人他连讲道理的机会的没。其实这只能怪李中吾社会经验太少了,他乡下的黑社会只算未入流的跑龙套的黑社会,而他刚才碰到的,却是有牌照的职业的黑社会,如果开个玩笑的话,这种黑社会可以称之为“奉旨横行”。
没办法,李中吾只能灰溜溜的回了家,今天总算也并不是毫无收获,也许是那些正牌黑社会看不起他那几个馒头烂苹果,虽然肮脏了点,不过他今天的晚餐终于有着落了。只是回来后,他看着拐伯那还未能下殓的尸体,他不禁又悲从中来。幸亏现在已是腊月,天气已很冷了,尸体一天两天还不至于会腐败的。
自怨自责中,李中吾好半夜才在迷迷糊糊中睡去。
接下去的几天,那个镇关西都不知是不是看上了他,或是怪他连点小小表示都没有,太不会做人,反正李中吾天天地摊上的书都被光荣的美其名曰充了公。
李中吾即使是个再不懂世故的人,有了这几天的经历,也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的性格却是跟他老爸一样,一条牛筋硬到底,吃软不吃硬的。象他这种人,如果他真的服了你,那你要他如何都可以。如果他不服你,即使你官再大再有钱,他都是嗤之以鼻的。郑屠这些伎俩,对于已研究了几十年人性及极度清高的李中吾来说,那会就这样屈服了。
此处不容爷,自有容爷处。渭州府不让俺摆摊,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呀。所以这天,李中吾就不辞辛劳的到了京城摆摊了。
但他果然躲不起,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想不到,连天下的城管都一般黑。想不到,京城的城管反而水平更高,李中吾赶了大半天的路,将书摊摆好后,刚闭上眼想打个盹儿,一睁开眼,就看到戴着大盖帽的大汉,已经将他的书成捆的拎走了,手法之纯熟速度之迅快,绝不是渭州府郑屠这种乡巴佬能比的。
李中吾实在气急,以他都想不到的速度弹跳起身,疾奔过去欲讨个说法,谁知他刚一近身,也不知那帮盖帽中谁起了一飞脚,他就被射出三尺,昏迷过去了。想来这些人平时也练惯了武功,如此高深武功却又是郑屠之流绝对汗颜的。
当他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市集上的人都几乎走光了。看来京城里的更是人情淡漠,他躺了这么久,居然没有一个人过来理睬下他。在渭州府至少还有人施舍几个果子馒头给他充饥,到这里不但挨了揍看来还要挨饿。
李中吾好不容易才爬起身来,只感到胸口又传来一阵剧痛,这些城管想来平时都不怎么当小贩是人,下手如此之狠,要不是他胸口前还掖着那本须臾不离身的厚厚的《厚黑学》,卸去了不少力道,这一脚就会让他有断骨之虞。李中吾不由心里苦笑,想不到这本书竟会以这种方式帮助了他一下。但现在又疼又饿天色又暗了,今晚看来是回不了渭州,只能在京城呆一晚了。而且他也明白,除非今晚能找个地方投宿,否则现在这种天气,日落后气温将下降很快,今晚如果露宿街头的话,明天他的结局可能就会象拐伯一样,再也爬不起来了。
性命攸关,现在是什么面子、顾虑都要放下了,有什么比连命都没了更重要呢?李中吾还不至于弱智僵化到那种地步,但他毕竟都隐居很多年了,有来往的人毕竟少得可怜,
李中吾煞是一番搜肠刮肚,终于想起,旧时私塾中有位旧学叫秦烩的,现时正在京城当官,于是一番问询寻觅,终给他寻到秦烩府上。
这时李中吾也已有几分酒酣耳热,见秦烩惶然无状,心道原来不但自己,原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在江湖飘,都不是太容易的事啊。他现在已不记得自己比别人混得更不如意了,忽然感觉自己已经立地成佛般,对秦烩颇起了股同情之心,或许他还有点虚荣之意,其实这世上谁人没有虚荣心呢?衣锦夜行那不过是一个笑话,人们对于自己达不到却又想达到的一种境界的憧憬罢了,这种境界跟马克屎的共产主义,跟某位姓某的,说什么我不喜欢别人崇拜我,但却让别人山呼万岁的家伙一样,都是虚伪的骗小孩的。
至少他们就没有李中吾那么老实,因为李中吾现在已很得意的从他怀中掏出那本他视如命根子般,连跟了他几十年的拐伯都只闻其名未见真容的《厚黑学》道,“秦兄,不必烦心,小弟不才,不过小弟这一本几十年精研而成的大。。。大。。。大文〈厚黑学〉可能会帮到你。”他本来很想说大作,但终于还未醉到不清醒,想起这篇东东都未经过官方媒体确认,CCAV也未作正式报道,怎能自称大作,所以,吱唔之下,虽然再不愿意,也只能算大文了。
但他这一掏出来,连秦烩这种生有鼻窦炎的都觉得有点难顶,如果不是出于礼貌,几乎就要掩鼻而走。皆因这本书被李中吾一直掖于怀里,久受他那一年未清理的狐臭熏陶,那味道实在有点夸张。但秦烩毕竟是混了几十年官场的人,早已练得喜怒不形于色,见李中吾颇当回事样子,表面上也客气感谢了番,将书纳了。
两人又喝得几杯,夜已渐阑,席散。秦烩吩咐下人安排了李中吾宿处,也自归寝。
夜半,秦烩忽然头痛而醒,想是昨晚酒喝多了,虚火上升。此后再不能寐,颇是烦躁。无奈,唯有找本书来看看解闷。这时他的目光落到床前小桌桌面上,李中吾那花费几十年心血的大文《厚黑学》赫然正摆在上面,秦烩本来对他的那番说辞颇不以为然,想想一个连饭都几乎吃不饱的穷酸书生,能写出什么成功的文章呢?还说什么研究了几十年,不过是读书人惯于夸夸其谈的牛皮吧。
对于李中吾的这本书,秦烩只不过当时不好拒绝,出于礼貌接了过来,想想李中吾既然好象当宝一般,也不好太落他的面子,暂且放个两天敷衍一下再还给他吧。不过现在他想也没有其他什么书好看,不妨翻翻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
谁知一翻之下,秦烩只觉这书竟是字字珠玑,奥妙无穷,其间关于三国时曹操、孙权、刘备及楚汉时刘邦和项羽的权谋相斗、时运命格的描写,对于自己的现状,竟似颇有启迪现实意义。秦烩只看得爱不释手,不觉间已是日上三竿了,犹浑然不觉。
这时门外忽传来一阵敲门声,方将秦烩惊醒过来,开门看时,原来家僮久未见他出来,过来催他用膳。秦烩又命家僮去叫李中吾。
两人用膳完毕,李中吾想起家里拐伯下葬之事,犹豫之下,方待开口,谁料秦烩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先他一步开了口。这时只听秦烩一脸讨好的道:“中吾兄昨晚借阅小弟的那本《厚黑学》,果是旷世奇书,小弟欲以十金跟兄购买。”李中吾未料到他会说这事,他辛苦了几十年,现在也就一本《厚黑学》,怎能轻易卖与他人,不由面有难色。
秦烩看他神态,以为自己价钱出得太低,急又接口道:“三十金,小弟知道此乃吾兄耗费数十年之心血结晶,本不欲夺兄之所爱,实在因小弟太过喜欢这书,万望吾兄体谅小弟这一番诚心,不吝赐购。”
李中吾想不到自己这书这么值钱,又见秦烩说得如此情真意切,自己今又正等钱用,拒绝一词,却也是说不出口。沉吟了半晌,方道:“多谢烩弟对敝人的涂鸦之作如此厚爱,非是吾不肯割爱,皆因此书只得一本,如果赠了予烩弟,兄不复有矣,如何是好?“
果然是读书人,卖都可以说成赠。秦烩此时倒没注意到这点,听李中吾语气中并无回绝之意,心下大喜,不过李中吾所说是真。秦烩脑筋倒也转得快,略略深思下后,道:“兄台所言极是,弟有一法,兄台今天暂且在小弟处多住一晚,容弟再尽点东道之谊,然后我叫人紧急临摹一本,如此可好?”
李中吾看秦烩一副志在必得的紧张样子,不禁心里颇有点成就感,看来自己写了几十年的书确非垃圾,连堂堂的所谓“内阁中书大学士”都当宝一般。这时他忽然起了点坏心,有点半开玩笑不情好意的道:“烩弟如此喜欢为兄的书,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只是为兄自小就少出远门,对于陌生床褥实在有点住不惯,昨晚俺就通宵难眠,辛苦得紧,如果烩弟今晚可让芙蓉。。。芙蓉陪为兄一聊,长夜漫漫相信也不再孤枕难眠矣!”
“芙蓉,你说那个芙蓉?”秦烩却一时会不过意来,愕然问道。李中吾有点不好意思的应道:“就是昨天席间,烩弟府上端菜的那个婢女芙。。。芙蓉。。。”“哈。。。”秦烩差点笑出声来,“你是说那位大嫂???不。。不。。。那位上菜的美女芙蓉?。。。。”,“正是,正是那位芙蓉姐姐。”。
秦烩不禁心里暗叹,真是人心不古,想不到这李中吾学兄满腹才华,竟也是个色中饿鬼,连芙蓉这种下三滥的货色都不放过,真有“有杀错不放过”的豪情胜慨矣,或许跟历史上颁布过“七杀令”的张献中和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蒋阶石有得一比。
对于芙蓉姐姐此等恐龙货色,秦烩平时几乎连正眼都不会看下,怕看了眼睛会生痔疮,李中吾此等简直不是要求的要求,他那会不答应。他却那知李中吾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处级干部,就算见到个老母猪都会产生性幻想的。昨天在秦烩府中,芙蓉又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女人,也许算一见钟情吧。虽然那芙蓉姐姐在别人眼中,蒜头鼻厚嘴唇,木瓜胸河马臀,年纪不小肤色不白,实在找不出什么优点。但俗话说各花入各眼,李中吾对于女性方面,经验实在等同于小学一年级生水平而已,故芙蓉在他眼中,已是绝色。
那一夜他跟芙蓉无限旖妮,自不必说。
第二天一早,秦烩的家丁终于连夜赶工将《厚黑学》临摹完成,李中吾收了秦烩那三十金,回去后终将拐伯风光下殓,日后他的《厚黑学》一书,比之《哈利.波特》更畅销全球,终成一代富贾,后又风光迎娶了占有他初夜权的芙蓉姐姐为妻,当然,此是后话,此间不表。但凭《厚黑学》此书成功的却并非只有李中吾一个,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秦烩得到《厚黑学》的摹本后,也是日夜钻研,较之他当年参加科举更为用功。不消一年,终于被他将其中精髓领会不少,秦烩将其中心得体会用于实践,行贿受贿,擦鞋溜须,夤缘钻刺,口蜜腹剑等无不得心应手,当年一心埋头工作不受重用,想不到如此竟深得晕宗开心,自此后官运亨通,一路攀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职矣。
此时秦烩想起这些旧事,心下竟似有点惆怅。不过这一念头转瞬即没。他又想起李中吾向他索要芙蓉之事,心下不由一动,道李中吾能做的事,自己如何做不得。自己都五十多岁了,即使现在已贵为丞相,又还能享受多久呢?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自己先享受个够再说吧,理得它天朝江山如何倾覆飘摇、衰败没落。
看来《厚黑学》可能真是本危险的书,如果理解错误的话,也许会将人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秦烩多年沉淫此书,几乎已将原本做人的一点良心都掉失殆尽,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坏点子了。
次日,杀皇又在宫中排筵,宴请秦烩。席间杀皇还是绝口不提和约之事,但秦烩经过昨夜一番思量,心里早有了主意。酒过三巡之后,秦烩借点酒意,向杀皇老实不客气,恬不知耻的道:“杀皇陛下,老臣离开中原日久,虽近来承蒙陛下厚待,不胜感激及惶恐,但思乡之心日炽。和约之事,老臣拟早早签定了,以便早日归去。只是老臣有个有情之请,老臣曾有一晚在自己所居寝舍,偶遇一身带异香之贵国女子,后再不见其芳踪,令老臣颇是念念不忘,希陛下能将其恩赐予俺,如此定将永铭深恩,感激涕零!”
听秦烩老脸都不红地说完这一段话,杀皇眼里似乎急速地掠过一丝怒意,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这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一闪即逝,秦烩虽然惯于察言观色,这一下却并没留意到。一来是他正自顾自的说话,二来是他现在满脑子所充斥的,都是那晚跟那位神秘女郎在一起时的香艳风光。
这时杀皇忽然一阵哈哈大笑,才将秦烩从迷思中惊醒过来,只听杀皇朗声道:“秦爱卿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秦爱卿已答应签订和约,区区一个女。。。女子,本人自不会吝啬,她能被许配给秦爱卿,这是她几世修来的福份呀,到时自当让她跟你回国。和约之事,等咱们喝完酒后孤王再安排人手跟爱卿办理吧。来来来,咱们再多干几杯。。。哈哈哈。。。”
席间又是一阵此起彼落的劝酒碰杯声。
秦烩得了杀皇应诺,中午休息过后,就在中鹅不平等条约上签了字。可叹天朝包括库衩岛在内,经过无数代人开疆拓土,不知付出多少艰辛牺牲才得以拥有的四十多万大好领土,就因为秦烩这一已色欲,在他随手轻轻一挥之下,就这样白白的送给了鹅人。
杀皇果然也信守承诺,当晚那位神秘女朗果然又如期出现在了秦烩房中,秦丞相花了天朝如此大的代价,才又可以跟美人再度春宵,那夜里高潮迭起,搏尽老命之乐事,不须赘言。
次日,秦烩起床后,心怕鹅人吃言,急急的命下人打点好行装,办理好各种手续,就迅速举团返国了。
路上自是一番辗转奔波,但秦烩有波霸小鸡一路相伴,只感无比快乐,那有丝毫劳顿感觉,只觉归程较之去程近了何止两倍,这晚已回到京师,俱各用膳休息了。
夜半,秦烩跟波霸小鸡又大战了一回合后,正又累又困的合上双眼,这时忽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秦烩无可奈何的开门看时,却是府里门僮,正气喘吁吁、神色紧张的站在门口。秦烩不由勃然大怒,正欲狠狠的斥责几句,然后叫人抓下去打五十大板。
这门僮也忒大胆,居然敢在此时来扰他好梦,难道活得不耐烦了?
那门僮未待他开口,却已连珠炮般急忙报告说:“禀相爷,皇。。。皇上来了,正在大厅等。。。等侯相爷呢?”
秦烩不由听得心下一惊,想不到自己刚回来皇上就知道了,夤夜来访,这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呀,有什么事这么紧急呢?难道是皇上已收到信报,知道自己在鹅国人的和约上签了字,现在特意过来问罪的?要不是,又什么事这么急要半夜过来呢?
秦烩心里颇是惶然无状,忐忑不安。但皇上驾临,又那到他慢慢思量,只好急急的整衣束冠,赶来见驾。
君臣见礼上茶宣喧完毕,秦烩偷眼瞧了瞧晕宗,却见晕宗脸上似并没怒意,甚至似还隐隐有点笑意,秦烩心下稍安,但却不知晕宗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心里颇是纳闷。
还好晕宗并没让他纳闷太久,因为现在他似乎已有点迫不及待的开口了:“据说爱卿今次出使鹅国,杀皇赠予爱卿一身带异香、美艳绝伦的奇女子,为什么你不让他出来见下本王呢?难道想当着本王的面金屋藏娇不成?嘿嘿嘿。。。”
原来如此,秦烩本来还绷着的心不由一松,晕宗夤夜来访并非问罪而来。但他心里却很快又腾起一丝怒气,看来天朝真没得救了。这昏君一心关心的原来不过是美女,政事倒一点不提,唉!
秦烩怒归怒,而且他也不想想自己也不过是如此货色。
不过他面上倒是一点都没表现出来。皇上既然如此吩咐了,他又怎敢违抗,忙面上堆笑道:“皇上英明,这么快就收到消息了,小子岂敢在皇上面前藏私,只是今晚准备略作休息,明天再带他上宫见驾而已。”言毕,他即命家僮去传婆霸小鸡。秦烩这时心里已知不妙,晕宗其实说得没错,他本来就想金屋藏娇的,但既然已被晕宗知道了,想来自己的艳福也到头了,秦烩心下恼怒又不舍,但他城府极深,面上却始终是副恭谨模样。
不多时,忽然满室异香,原来婆霸小鸡已到,她也许是刚小寐醒来,脸上还留着抹温暖的红晕,鬓发因为未及整理有点散乱,却令她更显天然姿色,充满野性诱惑。秦烩一见,想起刚才这个尤物在自己胯下寻欢的销魂之态,不觉下体又起了丝反应。
但在晕宗面前,他却不敢有太大反应,忙强压下那股心猿意马,有点尴尬的向晕宗瞧去。
晕宗自是不必掩饰的,秦烩虽知他好色,但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却还是第一次,所以他乍看之下,差点也被吓了一跳。
但见晕宗此时就如只饿极的狮子见到只肥美无比的羚羊般,眼里尽是贪婪掠夺之意,大有一口噬之而后快的气势。令人感到有点滑稽的是,晕宗却又象被人点了穴,这时又有点痴痴呆呆样子,嘴巴半张着,连口水都垂了几串下来。
看他这模样,连同为色中饿鬼的秦烩都不禁暗自摇头,心道,“这样也太失态了吧,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当着众人之面,无耻下流到如此地步!”
秦烩思念未歇,这时厅里响起一阵鸟语鸳声:“奴婢见过皇上,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却见波霸小鸡正学中原女子礼节,向晕宗道了个万福。晕宗此时方恍然醒转,听得这异国艳女竟会中原语言,而且又如此乖巧知趣,心下更喜。早忍不住走了近来,双手将波霸小鸡扶住,有点语无伦次的道:“爱卿。。不。。美人。。。姑娘免礼。。。”
秦烩看他那语气神态,心道完了,胸中怒气更盛,却又发作不出,只觉喉咙一甜,也只好努力忍住,又咽了回去。
幸亏晕宗这时注意力全在小鸡身上,并没注意到秦烩这时一张脸都涨成了猪肝色,否则秦烩说不定就要有好果子吃了。
晕宗这时忽呵呵大笑道:“秦爱卿这次出使鹅国,为本王寻得如此佳人,应算一功,孤王就不追究你签约割土之事了,来人呀,护送美人起驾回宫。”
言罢,也不理秦烩正欲匍匐谢恩,连万岁都未说完整,就拉着波霸小鸡的手,上了自己的辇毂
,扬长而去了。
秦烩看他去远,刚才一口强忍下的鲜血,才狂喷了出来。他明白,晕宗才不理又掉了多少国土这些事,以前经过自己的手签不平等条约,都不知掉失了多少国土了,这次还算掉得少的,晕宗只觉老祖宗的土地,掉了也不心痛的,何况这昏君总觉得天朝地大物博,送点土地给别人又有何妨,他喜欢的只是美酒佳人,珍珠宝玩而已。
秦烩跟了他这么久,他的那些嗜好岂会不知,这次他出使鹅国,其实也搜罗了不少鹅国美女,还有杀皇也送了他不少金银珠宝,本来想明天将这些美女宝贝送些给晕宗,就可搪塞过关了。却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晕宗居然亲自过来带走了他这次带回来的最宝贵的宝贝,秦烩如何能不吐血。但晕宗毕竟是皇上,吐血又能怎么样呢?晕宗走后,秦烩愣怔了大半夜,在心里诅咒毒骂了晕宗无数次,终于还是失魂落魄、万般无奈的回去睡了。
秦烩一世奸相,这种无奈的心情算比较少有的了,因为他刚才居然在想,波霸小鸡落到晕宗手上,晕宗出名的性虐待人物,整天叫人帮他搜罗些性趣用具,这个没人比秦烩更清楚的,因为他就是掌管这方面的头头。他明白,那些性用具比如老虎橙之类,是如何的灭绝人性。这些日子下来,秦烩虽然不是一夜夫妻百日恩,但居然已对小鸡生出了点感情,想到小鸡将会被晕宗这个比他更狠的色狼如何虐待,刚才竟然掉了几滴鳄鱼泪。
唉,问世间情为何物。。。。。。
但居然连他这种自认天下第一才子第一聪明的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世上还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
没办法,李中吾只能灰溜溜的回了家,今天总算也并不是毫无收获,也许是那些正牌黑社会看不起他那几个馒头烂苹果,虽然肮脏了点,不过他今天的晚餐终于有着落了。只是回来后,他看着拐伯那还未能下殓的尸体,他不禁又悲从中来。幸亏现在已是腊月,天气已很冷了,尸体一天两天还不至于会腐败的。
自怨自责中,李中吾好半夜才在迷迷糊糊中睡去。
接下去的几天,那个镇关西都不知是不是看上了他,或是怪他连点小小表示都没有,太不会做人,反正李中吾天天地摊上的书都被光荣的美其名曰充了公。
李中吾即使是个再不懂世故的人,有了这几天的经历,也看出了其中的猫腻。他的性格却是跟他老爸一样,一条牛筋硬到底,吃软不吃硬的。象他这种人,如果他真的服了你,那你要他如何都可以。如果他不服你,即使你官再大再有钱,他都是嗤之以鼻的。郑屠这些伎俩,对于已研究了几十年人性及极度清高的李中吾来说,那会就这样屈服了。
此处不容爷,自有容爷处。渭州府不让俺摆摊,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呀。所以这天,李中吾就不辞辛劳的到了京城摆摊了。
但他果然躲不起,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想不到,连天下的城管都一般黑。想不到,京城的城管反而水平更高,李中吾赶了大半天的路,将书摊摆好后,刚闭上眼想打个盹儿,一睁开眼,就看到戴着大盖帽的大汉,已经将他的书成捆的拎走了,手法之纯熟速度之迅快,绝不是渭州府郑屠这种乡巴佬能比的。
李中吾实在气急,以他都想不到的速度弹跳起身,疾奔过去欲讨个说法,谁知他刚一近身,也不知那帮盖帽中谁起了一飞脚,他就被射出三尺,昏迷过去了。想来这些人平时也练惯了武功,如此高深武功却又是郑屠之流绝对汗颜的。
当他醒来时,已是黄昏时分了,市集上的人都几乎走光了。看来京城里的更是人情淡漠,他躺了这么久,居然没有一个人过来理睬下他。在渭州府至少还有人施舍几个果子馒头给他充饥,到这里不但挨了揍看来还要挨饿。
李中吾好不容易才爬起身来,只感到胸口又传来一阵剧痛,这些城管想来平时都不怎么当小贩是人,下手如此之狠,要不是他胸口前还掖着那本须臾不离身的厚厚的《厚黑学》,卸去了不少力道,这一脚就会让他有断骨之虞。李中吾不由心里苦笑,想不到这本书竟会以这种方式帮助了他一下。但现在又疼又饿天色又暗了,今晚看来是回不了渭州,只能在京城呆一晚了。而且他也明白,除非今晚能找个地方投宿,否则现在这种天气,日落后气温将下降很快,今晚如果露宿街头的话,明天他的结局可能就会象拐伯一样,再也爬不起来了。
性命攸关,现在是什么面子、顾虑都要放下了,有什么比连命都没了更重要呢?李中吾还不至于弱智僵化到那种地步,但他毕竟都隐居很多年了,有来往的人毕竟少得可怜,
李中吾煞是一番搜肠刮肚,终于想起,旧时私塾中有位旧学叫秦烩的,现时正在京城当官,于是一番问询寻觅,终给他寻到秦烩府上。
这时李中吾也已有几分酒酣耳热,见秦烩惶然无状,心道原来不但自己,原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在江湖飘,都不是太容易的事啊。他现在已不记得自己比别人混得更不如意了,忽然感觉自己已经立地成佛般,对秦烩颇起了股同情之心,或许他还有点虚荣之意,其实这世上谁人没有虚荣心呢?衣锦夜行那不过是一个笑话,人们对于自己达不到却又想达到的一种境界的憧憬罢了,这种境界跟马克屎的共产主义,跟某位姓某的,说什么我不喜欢别人崇拜我,但却让别人山呼万岁的家伙一样,都是虚伪的骗小孩的。
至少他们就没有李中吾那么老实,因为李中吾现在已很得意的从他怀中掏出那本他视如命根子般,连跟了他几十年的拐伯都只闻其名未见真容的《厚黑学》道,“秦兄,不必烦心,小弟不才,不过小弟这一本几十年精研而成的大。。。大。。。大文〈厚黑学〉可能会帮到你。”他本来很想说大作,但终于还未醉到不清醒,想起这篇东东都未经过官方媒体确认,CCAV也未作正式报道,怎能自称大作,所以,吱唔之下,虽然再不愿意,也只能算大文了。
但他这一掏出来,连秦烩这种生有鼻窦炎的都觉得有点难顶,如果不是出于礼貌,几乎就要掩鼻而走。皆因这本书被李中吾一直掖于怀里,久受他那一年未清理的狐臭熏陶,那味道实在有点夸张。但秦烩毕竟是混了几十年官场的人,早已练得喜怒不形于色,见李中吾颇当回事样子,表面上也客气感谢了番,将书纳了。
两人又喝得几杯,夜已渐阑,席散。秦烩吩咐下人安排了李中吾宿处,也自归寝。
夜半,秦烩忽然头痛而醒,想是昨晚酒喝多了,虚火上升。此后再不能寐,颇是烦躁。无奈,唯有找本书来看看解闷。这时他的目光落到床前小桌桌面上,李中吾那花费几十年心血的大文《厚黑学》赫然正摆在上面,秦烩本来对他的那番说辞颇不以为然,想想一个连饭都几乎吃不饱的穷酸书生,能写出什么成功的文章呢?还说什么研究了几十年,不过是读书人惯于夸夸其谈的牛皮吧。
对于李中吾的这本书,秦烩只不过当时不好拒绝,出于礼貌接了过来,想想李中吾既然好象当宝一般,也不好太落他的面子,暂且放个两天敷衍一下再还给他吧。不过现在他想也没有其他什么书好看,不妨翻翻究竟是什么东东来的?
谁知一翻之下,秦烩只觉这书竟是字字珠玑,奥妙无穷,其间关于三国时曹操、孙权、刘备及楚汉时刘邦和项羽的权谋相斗、时运命格的描写,对于自己的现状,竟似颇有启迪现实意义。秦烩只看得爱不释手,不觉间已是日上三竿了,犹浑然不觉。
这时门外忽传来一阵敲门声,方将秦烩惊醒过来,开门看时,原来家僮久未见他出来,过来催他用膳。秦烩又命家僮去叫李中吾。
两人用膳完毕,李中吾想起家里拐伯下葬之事,犹豫之下,方待开口,谁料秦烩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先他一步开了口。这时只听秦烩一脸讨好的道:“中吾兄昨晚借阅小弟的那本《厚黑学》,果是旷世奇书,小弟欲以十金跟兄购买。”李中吾未料到他会说这事,他辛苦了几十年,现在也就一本《厚黑学》,怎能轻易卖与他人,不由面有难色。
秦烩看他神态,以为自己价钱出得太低,急又接口道:“三十金,小弟知道此乃吾兄耗费数十年之心血结晶,本不欲夺兄之所爱,实在因小弟太过喜欢这书,万望吾兄体谅小弟这一番诚心,不吝赐购。”
李中吾想不到自己这书这么值钱,又见秦烩说得如此情真意切,自己今又正等钱用,拒绝一词,却也是说不出口。沉吟了半晌,方道:“多谢烩弟对敝人的涂鸦之作如此厚爱,非是吾不肯割爱,皆因此书只得一本,如果赠了予烩弟,兄不复有矣,如何是好?“
果然是读书人,卖都可以说成赠。秦烩此时倒没注意到这点,听李中吾语气中并无回绝之意,心下大喜,不过李中吾所说是真。秦烩脑筋倒也转得快,略略深思下后,道:“兄台所言极是,弟有一法,兄台今天暂且在小弟处多住一晚,容弟再尽点东道之谊,然后我叫人紧急临摹一本,如此可好?”
李中吾看秦烩一副志在必得的紧张样子,不禁心里颇有点成就感,看来自己写了几十年的书确非垃圾,连堂堂的所谓“内阁中书大学士”都当宝一般。这时他忽然起了点坏心,有点半开玩笑不情好意的道:“烩弟如此喜欢为兄的书,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只是为兄自小就少出远门,对于陌生床褥实在有点住不惯,昨晚俺就通宵难眠,辛苦得紧,如果烩弟今晚可让芙蓉。。。芙蓉陪为兄一聊,长夜漫漫相信也不再孤枕难眠矣!”
“芙蓉,你说那个芙蓉?”秦烩却一时会不过意来,愕然问道。李中吾有点不好意思的应道:“就是昨天席间,烩弟府上端菜的那个婢女芙。。。芙蓉。。。”“哈。。。”秦烩差点笑出声来,“你是说那位大嫂???不。。不。。。那位上菜的美女芙蓉?。。。。”,“正是,正是那位芙蓉姐姐。”。
秦烩不禁心里暗叹,真是人心不古,想不到这李中吾学兄满腹才华,竟也是个色中饿鬼,连芙蓉这种下三滥的货色都不放过,真有“有杀错不放过”的豪情胜慨矣,或许跟历史上颁布过“七杀令”的张献中和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蒋阶石有得一比。
对于芙蓉姐姐此等恐龙货色,秦烩平时几乎连正眼都不会看下,怕看了眼睛会生痔疮,李中吾此等简直不是要求的要求,他那会不答应。他却那知李中吾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处级干部,就算见到个老母猪都会产生性幻想的。昨天在秦烩府中,芙蓉又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女人,也许算一见钟情吧。虽然那芙蓉姐姐在别人眼中,蒜头鼻厚嘴唇,木瓜胸河马臀,年纪不小肤色不白,实在找不出什么优点。但俗话说各花入各眼,李中吾对于女性方面,经验实在等同于小学一年级生水平而已,故芙蓉在他眼中,已是绝色。
那一夜他跟芙蓉无限旖妮,自不必说。
第二天一早,秦烩的家丁终于连夜赶工将《厚黑学》临摹完成,李中吾收了秦烩那三十金,回去后终将拐伯风光下殓,日后他的《厚黑学》一书,比之《哈利.波特》更畅销全球,终成一代富贾,后又风光迎娶了占有他初夜权的芙蓉姐姐为妻,当然,此是后话,此间不表。但凭《厚黑学》此书成功的却并非只有李中吾一个,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秦烩得到《厚黑学》的摹本后,也是日夜钻研,较之他当年参加科举更为用功。不消一年,终于被他将其中精髓领会不少,秦烩将其中心得体会用于实践,行贿受贿,擦鞋溜须,夤缘钻刺,口蜜腹剑等无不得心应手,当年一心埋头工作不受重用,想不到如此竟深得晕宗开心,自此后官运亨通,一路攀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职矣。
此时秦烩想起这些旧事,心下竟似有点惆怅。不过这一念头转瞬即没。他又想起李中吾向他索要芙蓉之事,心下不由一动,道李中吾能做的事,自己如何做不得。自己都五十多岁了,即使现在已贵为丞相,又还能享受多久呢?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自己先享受个够再说吧,理得它天朝江山如何倾覆飘摇、衰败没落。
看来《厚黑学》可能真是本危险的书,如果理解错误的话,也许会将人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秦烩多年沉淫此书,几乎已将原本做人的一点良心都掉失殆尽,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坏点子了。
次日,杀皇又在宫中排筵,宴请秦烩。席间杀皇还是绝口不提和约之事,但秦烩经过昨夜一番思量,心里早有了主意。酒过三巡之后,秦烩借点酒意,向杀皇老实不客气,恬不知耻的道:“杀皇陛下,老臣离开中原日久,虽近来承蒙陛下厚待,不胜感激及惶恐,但思乡之心日炽。和约之事,老臣拟早早签定了,以便早日归去。只是老臣有个有情之请,老臣曾有一晚在自己所居寝舍,偶遇一身带异香之贵国女子,后再不见其芳踪,令老臣颇是念念不忘,希陛下能将其恩赐予俺,如此定将永铭深恩,感激涕零!”
听秦烩老脸都不红地说完这一段话,杀皇眼里似乎急速地掠过一丝怒意,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这不过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一闪即逝,秦烩虽然惯于察言观色,这一下却并没留意到。一来是他正自顾自的说话,二来是他现在满脑子所充斥的,都是那晚跟那位神秘女郎在一起时的香艳风光。
这时杀皇忽然一阵哈哈大笑,才将秦烩从迷思中惊醒过来,只听杀皇朗声道:“秦爱卿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秦爱卿已答应签订和约,区区一个女。。。女子,本人自不会吝啬,她能被许配给秦爱卿,这是她几世修来的福份呀,到时自当让她跟你回国。和约之事,等咱们喝完酒后孤王再安排人手跟爱卿办理吧。来来来,咱们再多干几杯。。。哈哈哈。。。”
席间又是一阵此起彼落的劝酒碰杯声。
秦烩得了杀皇应诺,中午休息过后,就在中鹅不平等条约上签了字。可叹天朝包括库衩岛在内,经过无数代人开疆拓土,不知付出多少艰辛牺牲才得以拥有的四十多万大好领土,就因为秦烩这一已色欲,在他随手轻轻一挥之下,就这样白白的送给了鹅人。
杀皇果然也信守承诺,当晚那位神秘女朗果然又如期出现在了秦烩房中,秦丞相花了天朝如此大的代价,才又可以跟美人再度春宵,那夜里高潮迭起,搏尽老命之乐事,不须赘言。
次日,秦烩起床后,心怕鹅人吃言,急急的命下人打点好行装,办理好各种手续,就迅速举团返国了。
路上自是一番辗转奔波,但秦烩有波霸小鸡一路相伴,只感无比快乐,那有丝毫劳顿感觉,只觉归程较之去程近了何止两倍,这晚已回到京师,俱各用膳休息了。
夜半,秦烩跟波霸小鸡又大战了一回合后,正又累又困的合上双眼,这时忽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秦烩无可奈何的开门看时,却是府里门僮,正气喘吁吁、神色紧张的站在门口。秦烩不由勃然大怒,正欲狠狠的斥责几句,然后叫人抓下去打五十大板。
这门僮也忒大胆,居然敢在此时来扰他好梦,难道活得不耐烦了?
那门僮未待他开口,却已连珠炮般急忙报告说:“禀相爷,皇。。。皇上来了,正在大厅等。。。等侯相爷呢?”
秦烩不由听得心下一惊,想不到自己刚回来皇上就知道了,夤夜来访,这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呀,有什么事这么紧急呢?难道是皇上已收到信报,知道自己在鹅国人的和约上签了字,现在特意过来问罪的?要不是,又什么事这么急要半夜过来呢?
秦烩心里颇是惶然无状,忐忑不安。但皇上驾临,又那到他慢慢思量,只好急急的整衣束冠,赶来见驾。
君臣见礼上茶宣喧完毕,秦烩偷眼瞧了瞧晕宗,却见晕宗脸上似并没怒意,甚至似还隐隐有点笑意,秦烩心下稍安,但却不知晕宗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心里颇是纳闷。
还好晕宗并没让他纳闷太久,因为现在他似乎已有点迫不及待的开口了:“据说爱卿今次出使鹅国,杀皇赠予爱卿一身带异香、美艳绝伦的奇女子,为什么你不让他出来见下本王呢?难道想当着本王的面金屋藏娇不成?嘿嘿嘿。。。”
原来如此,秦烩本来还绷着的心不由一松,晕宗夤夜来访并非问罪而来。但他心里却很快又腾起一丝怒气,看来天朝真没得救了。这昏君一心关心的原来不过是美女,政事倒一点不提,唉!
秦烩怒归怒,而且他也不想想自己也不过是如此货色。
不过他面上倒是一点都没表现出来。皇上既然如此吩咐了,他又怎敢违抗,忙面上堆笑道:“皇上英明,这么快就收到消息了,小子岂敢在皇上面前藏私,只是今晚准备略作休息,明天再带他上宫见驾而已。”言毕,他即命家僮去传婆霸小鸡。秦烩这时心里已知不妙,晕宗其实说得没错,他本来就想金屋藏娇的,但既然已被晕宗知道了,想来自己的艳福也到头了,秦烩心下恼怒又不舍,但他城府极深,面上却始终是副恭谨模样。
不多时,忽然满室异香,原来婆霸小鸡已到,她也许是刚小寐醒来,脸上还留着抹温暖的红晕,鬓发因为未及整理有点散乱,却令她更显天然姿色,充满野性诱惑。秦烩一见,想起刚才这个尤物在自己胯下寻欢的销魂之态,不觉下体又起了丝反应。
但在晕宗面前,他却不敢有太大反应,忙强压下那股心猿意马,有点尴尬的向晕宗瞧去。
晕宗自是不必掩饰的,秦烩虽知他好色,但在自己面前表现出来,却还是第一次,所以他乍看之下,差点也被吓了一跳。
但见晕宗此时就如只饿极的狮子见到只肥美无比的羚羊般,眼里尽是贪婪掠夺之意,大有一口噬之而后快的气势。令人感到有点滑稽的是,晕宗却又象被人点了穴,这时又有点痴痴呆呆样子,嘴巴半张着,连口水都垂了几串下来。
看他这模样,连同为色中饿鬼的秦烩都不禁暗自摇头,心道,“这样也太失态了吧,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当着众人之面,无耻下流到如此地步!”
秦烩思念未歇,这时厅里响起一阵鸟语鸳声:“奴婢见过皇上,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却见波霸小鸡正学中原女子礼节,向晕宗道了个万福。晕宗此时方恍然醒转,听得这异国艳女竟会中原语言,而且又如此乖巧知趣,心下更喜。早忍不住走了近来,双手将波霸小鸡扶住,有点语无伦次的道:“爱卿。。不。。美人。。。姑娘免礼。。。”
秦烩看他那语气神态,心道完了,胸中怒气更盛,却又发作不出,只觉喉咙一甜,也只好努力忍住,又咽了回去。
幸亏晕宗这时注意力全在小鸡身上,并没注意到秦烩这时一张脸都涨成了猪肝色,否则秦烩说不定就要有好果子吃了。
晕宗这时忽呵呵大笑道:“秦爱卿这次出使鹅国,为本王寻得如此佳人,应算一功,孤王就不追究你签约割土之事了,来人呀,护送美人起驾回宫。”
言罢,也不理秦烩正欲匍匐谢恩,连万岁都未说完整,就拉着波霸小鸡的手,上了自己的辇毂
,扬长而去了。
秦烩看他去远,刚才一口强忍下的鲜血,才狂喷了出来。他明白,晕宗才不理又掉了多少国土这些事,以前经过自己的手签不平等条约,都不知掉失了多少国土了,这次还算掉得少的,晕宗只觉老祖宗的土地,掉了也不心痛的,何况这昏君总觉得天朝地大物博,送点土地给别人又有何妨,他喜欢的只是美酒佳人,珍珠宝玩而已。
秦烩跟了他这么久,他的那些嗜好岂会不知,这次他出使鹅国,其实也搜罗了不少鹅国美女,还有杀皇也送了他不少金银珠宝,本来想明天将这些美女宝贝送些给晕宗,就可搪塞过关了。却不知如何走漏了风声,晕宗居然亲自过来带走了他这次带回来的最宝贵的宝贝,秦烩如何能不吐血。但晕宗毕竟是皇上,吐血又能怎么样呢?晕宗走后,秦烩愣怔了大半夜,在心里诅咒毒骂了晕宗无数次,终于还是失魂落魄、万般无奈的回去睡了。
秦烩一世奸相,这种无奈的心情算比较少有的了,因为他刚才居然在想,波霸小鸡落到晕宗手上,晕宗出名的性虐待人物,整天叫人帮他搜罗些性趣用具,这个没人比秦烩更清楚的,因为他就是掌管这方面的头头。他明白,那些性用具比如老虎橙之类,是如何的灭绝人性。这些日子下来,秦烩虽然不是一夜夫妻百日恩,但居然已对小鸡生出了点感情,想到小鸡将会被晕宗这个比他更狠的色狼如何虐待,刚才竟然掉了几滴鳄鱼泪。
唉,问世间情为何物。。。。。。
但居然连他这种自认天下第一才子第一聪明的人都没想到的是,这世上还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
相似主题
正在浏览此帖子的用户
当前在线: 4 (会员: 0, 游客: 4)